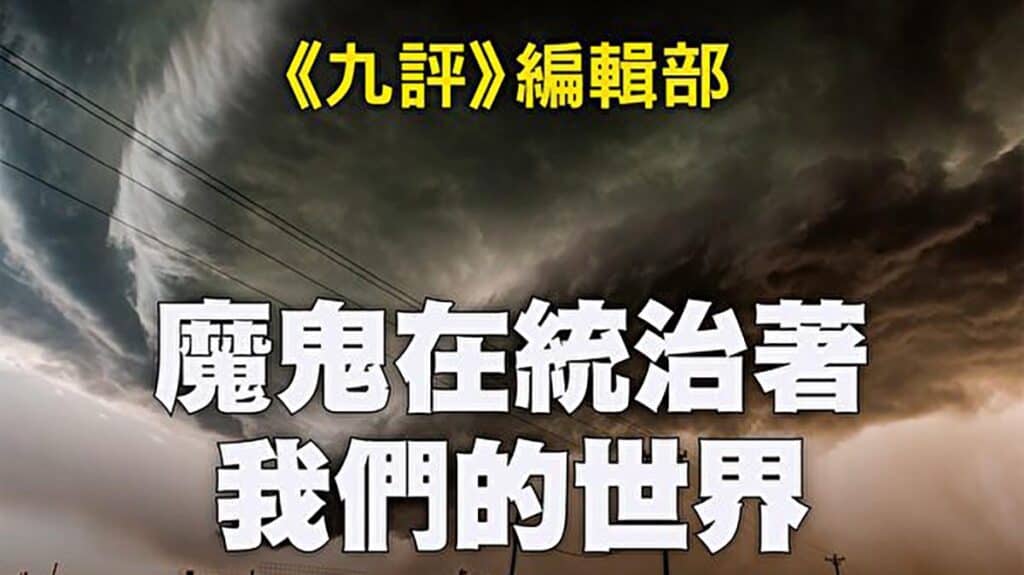上集我们从遇罗克的童年开始,了解了他的成长经历,他大量的读书,思考,并且敢于质疑和挑战,他清醒、冷静、成熟的如同一个思想家,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写出这样一篇引起巨大震动和反响的《出身论》。有一天,北京四中的学生找到遇罗文,说看了《出身论》很受感动,想要扩大宣传,最后,大家决定办一份报纸,报纸的名字就叫《中学文革报》。
1967年秋天,遇罗克甩开暗探,在北戴河。(图片来源:遇罗文)
“后来,他们想,好,出报纸是个好办法,那就出吧。我们就开始去买纸了。一到买纸才知道,纸根本就买不来,因为文革期间纸大部分都印毛选去了,还有给个学校发写大字报的纸。文化用品公司根本就没有纸可卖,那人就跟我诉苦说,我哪有纸卖给你们啊,可是他一看我们这篇文章,太欣赏了。那个人可能也是出身有问题,可是他无能为力。就在这时候,也就算是太巧了,有一个民主党派退一批纸。大概有五十领,一领大概有五百张。他说你们还不快把他那纸买下来,我就不给他办理退的手续,让他直接卖给你们。我们听这太好了,但是真到这时又发现没钱了,这纸得需要五百块钱。在当时,谁家有,谁家能舍得拿出来。我们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有办法,我到学校去借去。他就到学校跟学校领导说,我就是红卫兵,你们对 原来的红卫兵怎么对待,你也得对我怎么样。我想跟你借点钱,学校就真借给他五百块。我们有了纸了,就开始找印刷厂,印刷厂好找。”
办报纸的主要困难基本都解决了,遇罗克知道后非常兴奋,他连夜对《出身论》又做了仔细修改,1967年1月18号,铅印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终于问世了,而遇罗克的《出身论》整整占了报纸的三个版面。第一期报纸印了两万份,马上被抢购一空,兴奋至极的遇罗文和他的同学们又重印了一期专刊。
“印出了第一期两万份。紧接着是第二期又是两万份,这纸就全用光了。到第三期就没了,后来这时候就发愁了。我们就东找西找,包括也找到了蒯大富,但没有人能给我们提供,因为他们一看我们这篇文章说,你们这文章太危险了,你们太激进了,你们虽然说的是反血统论不假,但你们不光是反血统论,你们反的是党的阶级政策。我们不能提供。
留存下来的中学文革报复印本。(图片来源:遇罗文)
就在这时候,我就找到谁了呢?当时崇文区在全国有个组织叫全合总,他全称很长,全国合同工临时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些人呢绝大部分都是出身有问题。所以啊,他们可能能帮忙,而且这个组织发展的非常大。我找他们的时候,正好是在他们有势力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新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当时在北京是最大的印刷厂,我拿这封信找他还真起作用了,但是(新华印刷厂)说:你这就印几万份的报纸,我们没法帮你印。他说我们要印上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介绍到我们工厂的下属工厂去。我拿着他的介绍信,又找到了西城区,西四印刷厂,叫人民印刷厂。实际上是街道的,挂靠到新华社印刷厂。街道印刷厂都是出身不好的人才去了街道工厂嘛,他们一看这是中央报要来印的,他们乐坏了,大力支持,从此以后,我就不缺纸了。
当时卖报纸的场面非常感人,那简直人山人海。这几万份报纸一抢而空。2分钱一份,但黑市上多少钱,我就说不好,因为黑市上不讲花钱,它讲交换,我们这报纸一份能换五十份其他报纸。我们当时卖报纸是限量卖,不是说你能买多少买多少份,一人只能买十份。当时我们到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不是外地人多嘛,前面不有一片广场嘛,上面有花坛,然后我们就在花坛里边,让任何人不能进这里边来,因为怕大家挤你没法卖。我们这一帮人,有人专门数,十份一摞十份一摞,有几个人专门去递和收钱。一 会就把这好几万份卖掉了 。”
(旁白)当时这份报纸在北京城引起很大轰动,真的是一报难求,急于想得到《中学文革报》的人,只能在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两分钱一份的报纸。
报纸受欢迎的情况,遇罗文在他的回忆录《我家》中写了许多当时的细节,他说:
遇罗文(右)和弟弟遇罗勉(左)。(图片来源:遇罗文)
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到一份报纸,只有这么一份,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
卖报时,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印坏了的报纸也有人央求买走……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有个别在大街上给我们捣乱的,都被群众斥骂走了。
《中学文革报》在四中设立了一个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他们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和我们一起办报……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每天多达上千封,以致邮局不愿送了,我们只好自己去取。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从读者来信中就可以看出,不少人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当年就是在四川成都看到了刊登着《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
“你比如像胡平这样的,他在那印,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看他写文章我才知道他印,还有好多人把这么长的文章抄成大字报,二万多字的,你想得少天抄的,贴在街上,让大家看,大伙就是感受深,因为我不是刚才开头讲的,血统论怎么让大伙那么受害,突然有一个给你解放了,那你想大伙什么心情啊。别说让你干那些事,把命献出来,可能都会同意,等于在他一生中是太大的一件事了。所以我刚才就说,这有关血统论,这是中共干的所有罪恶里面的罪中之最,这个话题要说的话,不亚于犹太人被那个法西斯的迫害,这是在全世界里面可以说找不到类似可以跟那可比的东西了。你让这些人忆苦永远也说不完,可能比我说的更感人,这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遇罗锦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四中接待站讲述了他们四川地区血统论猖獗的程度,他坚决支持《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来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而且很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
接待站接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想了解《出身论》的作者,而《中学文革报》刊载的《出身论》署名只是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