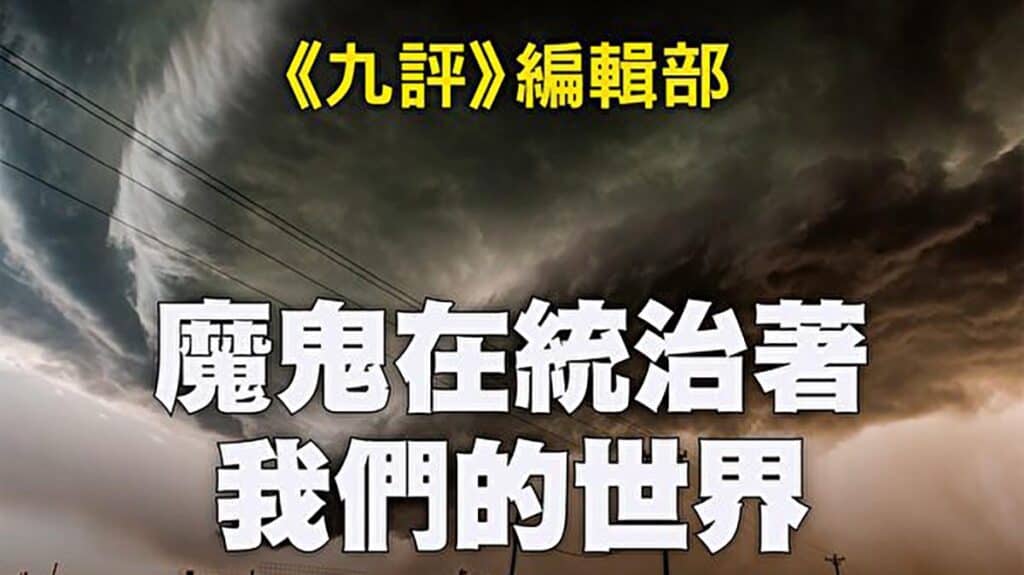中共在未夺得政权前,为了欺骗裹胁广大农民为其卖命打江山,便人为地煽动所谓“阶级仇恨”, 硬给农村合法拥有土地的人扣上一顶“地主” 的帽子,更说人家合法拥有的土地是“剥削” 农民而来,并承诺它若夺下政权便把这些土地和地主家的其它财产都拿来分给农民。使农村中一帮游手好闲、无能耐又想发财的流氓无产者,像着了魔一样地跟着中共,杀人、放火、造反,明火执仗抢劫,搞所谓“土改”,丧尽天良地整人,害人。结果 不但彻底摧毁消灭了中国农村中的精英——乡绅阶层,用粗俗的痞子文化取代了士绅文化,也把大量的民间财富搜刮一空。其中90%以上都流入党国官府手中,少数残汤剩莱如衣被,农具,日用品等物,农民也分得了一些好处,尤其是农民按人分得了田土,还慎重其事地颁发了所谓“田契”( 也就是土地所有证)给农民。上面盖有鲜红的官印。并说“这田土就永远归你所有了,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许多农民真是感动得痛哭流涕,甚至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中共“欲取先予”的欺骗手段。结果还没等农民高兴完,农业合作化运动便接踵而至。不过五、六年时间,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 化,其手段 更加凶残,不仅将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锅盆碗盏都一下全收归“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党国所有了。农民甚至在家生火做饭也不允许。一律到“公社食堂” 去吃一点少得可怜的“吊命饭”。什么“田契”, 更是废纸一张,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奴。农民这时才如梦初醒,但一切都晚了。1959至1961年间,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三千多万,刘少奇也急得向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啊”!
后来情况虽然一度有所缓和,解散了公社食堂,农民有了少量的自留地。但紧接着中共又在农村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社教运动”和什么“农业学大寨”。成天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连多养点家禽家畜都叫“走资本主义道路” 弄来批判斗争。农民没有了生产积极性,干农活便“磨洋工”。结果人哄地皮, 地哄肚皮, 年年减产歉收. 但官方不管你怎么减产歉收, 它要的公粮、统购、“八大提留”等一分也不能少。如此一来,把这些苛捐杂税全部上交以后,农民能分到手的那点粮食,等不到来年便已无粮断炊了。这是当年农村中的普遍现象。而土地贫脊的山区则更是雪上加霜。
本文要说的就是四川省宜宾县,凤仪乡一个叫许堰槽的地方。此地是不折不扣的穷山恶水。当地民谣都唱道:“有女不嫁许堰槽,不是吃包谷,就是吃红苕”。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批所谓“知青” 从城里下放到此,当时此地属凤仪公社, 凤仪公社是属于宜宾地区宜宾县管辖下的一个公社,有数千农民。凤仪公社地处宜宾西部,一条条绵延的群山横亘东西,公社革委会就座落在两边是高山的夹皮沟中。如果再往西几公里,便是云南的地界了。隆冬季节,沟北面陡峭的断头山上看不到几株成形的大树,山腰和山顶间或有一些积雪和墨绿灌木夹杂其间。南面的盖顶山,满眼全是一片黄绛色,一层一层环绕而上的豆沙土一眼望不到顶,一些残留在窄而浅薄沙土上零落的干玉米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据当地一位老农说,许堰槽的两边山上原来不是这样,那时满山都是青葱翠绿的参天大树,山上不时还有豹子出没。由于1958年全国总动员大办钢铁,许堰成了宜宾县大炼钢铁的第二个基地,把山上所有的树都砍光了,所以才落得现在这个样子。而今河滩上都还摆着几大堆当时炼铁时留下的矿渣。随着老农所指,东面无数个小山似的红褐色矿渣历历在目,至少占据了上百亩耕地,一片荒凉颓败的景象。
当时上山下乡落户在此公社的几十个知青分别插入各个生产小队,和农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着当地农民生活的劳苦和艰辛。农民们劳累了一天,还要抽时间做自留地。从早到晚忙里忙外,一年到头的辛苦。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不到一年就吃完了。由于缺乏油荤,更是饥饿难耐,青黄不接时,只好东挪西借想法填饱肚皮,实在想不出法的,只好挖野菜、刨蕨苔,千方百计弄吃的。还有的农民在自留地上种蕉藕来充饥。在缺衣少食的日子里,一些幽默一点的农民私下自嘲地说:“这磨骨头养肠子的日子哪天才能到头哦?”
农民们苦不敢言,是因为那时讲政治挂帅,谁也不敢乱说一句话。农民们还亲眼看到公社的一位姓王的副社长,就是因为在批斗会上呼错了一句口号,便当即被架飞机(反缚双手)来批斗,至今还在受到监管。
由于许堰槽生产队占地总面积200多亩,其中水田有50多亩,可耕种旱地80多亩,每年总产量6万斤左右。在全公社几十个生产队中数一数二。因此,上级政府根据全队总产量,规定该队应上交公粮1万多斤,上交统购粮7,000多斤。除交征购外,如果当年社员每人平均分上了500斤带壳粮,多余的粮食就必须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粮站,这叫“余粮”。虽然农民们心里不满,十分反感,但还是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这样一来,全生产队就几乎每家都会缺粮。为了吃饱肚子,生产队队委们铤而走险。队长召集大家开社员大会,并压低声音对社员们说:“我们队委会已开会商量决定,今年的粮食产量向公社革委会少报两万斤,不卖余粮,然后把这两万斤按人头、工分分给大家。如果哪个要去向公社革委会告密,我们全体社员就对他不起,叫他以后不好做人。这事,连我们队上的两位知青都积极支持。”在当时这就叫“瞒产私分”,即少报粮食产量,从而少向当局卖所谓的“余粮”。
本来农民自己生产的粮食,除了中共政府规定的所谓“公粮” 必须无偿地送给中共。这已经是野蛮地掠夺农民了。但当局还不满意,又巧立名目,规定农民还必须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一定数量的“余粮” 给中共当局。其实哪是什么“余粮”? 完全是在农民的口中夺食。农民敢怒而不敢言。这位队长此举就是以少报粮食产量从而少向中共卖粮,故曰“瞒产私分”,这在当时叫做“挖社会主义墙脚” 的“犯罪行为”。会被判刑劳改的,全国这类事早已时有发生。但农民为了活命,虽“明知山有虎”,也只好去铤而走险。就这样,那年生产队每人都多分得200多斤粮食,暂时缓解了农户的饥荒问题。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可能是由于生产队少卖了粮食,或许是有人向公社干部走漏了风声,但好像也没拿到确凿的证据。于是公社便派人到生产队了解当年收成的情况,并专门安排一个干部在队上“蹲点”, 所谓“蹲点” 就是住在队上进行调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有句风靡一时的流行语叫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这位“蹲点”的公社干部于是便来此处召开一场“诉苦大会”。 想用这种形式来启发农民的所谓“阶级觉悟”, 从而揭出是否有人在“挖社会主义墙脚”, 搞“瞒产私分” 这类“破坏活动”。在当时又叫做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所谓的“诉苦大会”终于开始。一天晚上,全生产队的农民都被召集来围坐在一间不足50平米的茅草公房里。靠土墙北面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两盏油灯。昏暗的灯光勉强能照满整间土屋,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气,令人感到窒息。蹲点干部端坐上方,先是一番文化大革命政治形势一派大好的报告,然后是一番要斗私批修,先国家后私人的党八股大道理。随后便动员大家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讲了今晚进行忆苦思甜大会的重要性。
由于这个生产队农民在划阶级成分时没有被划为大地主的,而仅有的两个划为小地主出租的农民都已在1960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只留下一个后人,没有符合被抓出来批斗的物件,农民们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血海深仇”。但主持人为了让诉苦大会开得有成效,便由队长安排贫协主席最先发言诉苦。
这位贫协主席年近六十,折皱的脸上满是花白的络腮胡。口里衔着叶子烟杆,烟头闪着丝丝亮点,缓缓地发出沙哑的声音。他说:“地主阶级剥削我们,地主阶级欺哄我们,在解放前确实有。你们年青人还不晓得,地主能把田地租给你,说明他还是相信你,是把你从头看到脚的。有些狡猾的地主还不把田地租给不讲信用,到时交不起租的贫下中农。只是在农忙时才请我们帮忙。当然,我们还不是要看啊,如果哪个地主对穷人凶,或太吝啬,我们还不是就不帮他,叫他请不到一个人。记得有一次,许堰下槽的一家地主请我去帮他栽秧子,我们几个帮工一早就下秧田,大概用了一袋烟功夫(约两个小时左右)就把一大块秧田的秧子全部扯上坎。这时狡猾的地主为了笼络收买我们,喊我们几个帮工烧烟了(即中途休息)。不一会儿,就叫他家人把猪儿粑(一种用糯米做成的食物)送到田头,说是让我们打腰火(中途加餐)。我们心里明白,这个地主明说是让我们几个帮工打腰火,其目的还不是想要我们吃饱了肚子,好多给他干活有力气呀。”这时,贫协主席顿了一下,突然提高了声音频率,“你们说,地主精明不精明?地主狡猾不狡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也好像说过,要吃小亏占大便宜,看来地主阶级和刘少奇真是一伙。”贫协主席说到这里,抬眼望了一下主持人,继续保持高频率的声音:“我们被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了,我们有些人不但不觉得,还认为地主阶级对我们好,这叫什么?这叫愚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结尾有点像是在呼口号,语音已近乎声嘶力竭了。
“就是!”贫协主席话刚落音,民兵排长马上接过话茬,“我还听我死去的幺爹说过,有一次,他在给地主薅秧子的时候,秧窝子已齐腰高了,那个狡猾的地主怕他薅秧子的时候偷懒,趁他还没有到田头,就先把一瓶酒和一碗回锅肉用一条长板凳放在大田的中间。地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怕你干活不踏实,马马虎虎,草草了事,没把整块田薅遍。如果你在薅秧时没有吃到地主事先放好的酒和肉,地主还要克扣你的工钱,你没吃到他放的酒和肉,就是扣工钱的证据,下次也不再请你了”。民兵排长抬眼望了一下主持人,然后对着在座的社员,大声说道:“你们说,地主奸诈不奸诈?坏心眼多不多?”会场一片沉默,其实此刻大家心里想的是:现在我们一个月还吃不上一回肉呢,要是谁能给我们一碗回锅肉还外加一瓶酒,那不是我们的大恩人,大救星了吗?
别看农民文化不高,实则很有幽默的智慧。贫协主席的那些话分明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回避追查瞒产私分这个要害,而民兵排长的那些话哪是在诉“旧社会” 之苦,分明是在说今不如昔;哪里是在说“地主坏”,分明是在说中共比过去的地主不知更坏、更可恶多少倍。事实摆在那里,沉默就是抗议。因此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既没有激起人们的什么“阶级仇恨”,更没人往瞒报粮食产量上扯。这使得那主持会议的公社干部十分失望,又无计可施。
突然,不知是谁放了一个声音又响、又长的响屁,而且声音在闷浊的空气中还很悠扬而自在地转了一个圈似的,大有“余音绕梁”之势,使在座的农民都憋不住笑出声来,会场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味。主持人见状,立即大声高呼起了口号:“我们一定要不忘阶级苦!”社员们也七零八落地跟着呼喊道“我们一定要牢记血泪仇!”不过社员们呼出的第二句口号声也渐渐不像主持人叫得那么响亮了……这场闹剧便就此收场。
此后蹲点的干部在生产队呆了好几天,到处摸底排查,但始终没有一个农民向他反映生产队瞒产私分的事情,他无可奈何,只好无功而返。因为农民们心里都明白,粮食是我们自己种的,为啥饭也吃不饱?你共产党好在哪里?我凭什么要信你的话?凭什么非要把粮交给你中共?所以要想不忍饥挨饿,只能瞒产私分。农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你中共干部不管什么花言巧语,革命道理也改变不了他们对“肚子饿了很难受,甚至要死人” 的那种担心与恐惧!这就是农民心中的“硬道理”!支援他们打赢了这场为了活命而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
--原载《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