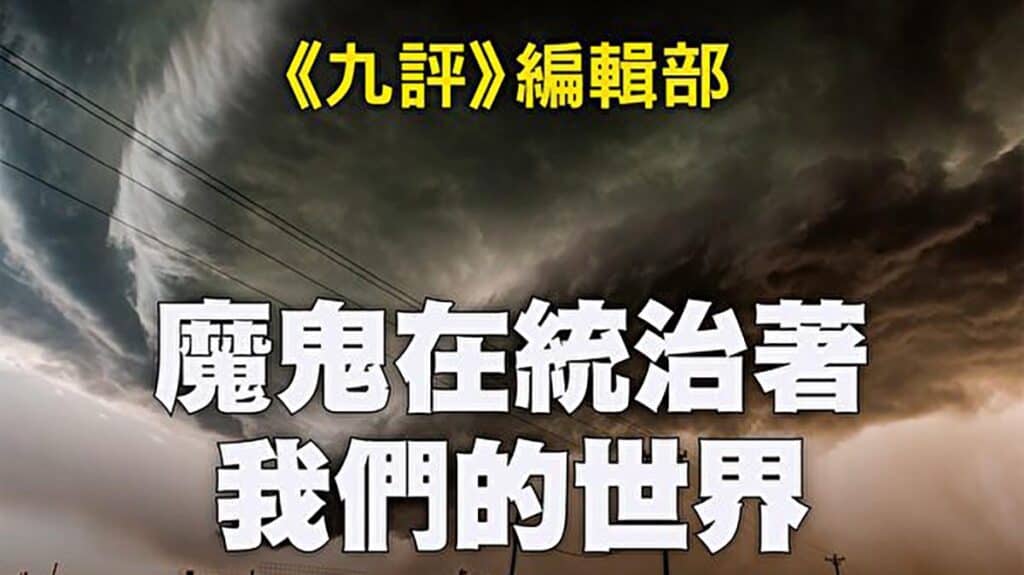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年5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指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信号预示,教师群体的巨大灾难即将来临。8月初,毛又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予以明确的支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北京各中学红色恐怖迅速升温,并在8、9月间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短短的时间内,仅北京市一地,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人数达1,772人,其中教师占绝大多数。
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内,提起北京被打死的教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卞仲耘其实不是教师,而是中共基层党组织的主要领导。网上可查见,卞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文革前任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常识表明,在中国的学校内,党的书记负责控制教师的思想。卞仲耘给学生开过哪门课?卞在教室内、在三尺讲台旁,有过给学生传道授业、讲课指导、答疑解惑的经历吗?没有!同样早已被蔽屏的是,1957年在卞书记领导的学校反右斗争中,北师大女附中究竟有多少教师曾被划为右派、遭受无情打击。
长期以来,人们完全忽略了卞仲耘作为中共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而将她当作受害教师寄予深深同情。文革中,灾难深重的教师通常可分三类。一类是专业学养稍显厚重,超出一般教师以上,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类是因捕风捉影的“历史问题”或“右派”分子;还有一类是因平素不愿靠拢组织,私下言论存有异见的“现行问题”。这些教师被统称为“牛鬼蛇神”,即便那些小心翼翼、未被归为“牛鬼蛇神”的教师,起码也属“臭老九”。卞仲耘作为早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基层领导人,不存在“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有“现行问题”,更谈不上“反动权威”,就连“臭老九”这一贱称,也与卞毫不沾边。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不是将卞仲耘当作教师中的“牛鬼蛇神”揪出来,而是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走资派”揪出来的。
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教师绝对是弱势群体,他们受迫害程度之深,至今令人唏嘘不已。全国范围内,教师被红卫兵任意批斗、围攻、毒打的事件,被社会广泛视作“革命行动”。现已渐入老年,口称“青春无悔”的“老三届”,全都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之中亲手殴打教师的凶手,也绝非少数。文革后整个社会对教师产生广泛同情,但对于文革中受冲击的各级官员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虽也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此种同情恐怕是极有限的。仅管现今中小学教师借助家教、补课、兴趣班等花样,大肆寻租捞钱;大学教师照本宣科、弄虚造假、骗取“课题经费”,更是公开秘密,但文革结束之初,整个社会对教师的同情,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卞仲耘被打致死的事件上,只要淡化她作为“中共基层领导”的真实身份,强调他作为教师的虚幻身份,在争取社会同情的策略方面,肯定可多得分。
女附中的高干子女居多,这批人即现今所谓太子党。他(她)们的父辈在红色政权建成后的最初六、七年内,即已织成无形的资讯关系网络,以便互通重要的政治资讯,作为选择行为策略的依据,以求自我保护。太子党们正是依仗上一代资讯资源优势,把握中南海新的态势,以便窥测方向,迅速在学校捕捉、瞄准斗争目标。卞仲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牺牲品。
1966年6月1日,中央台广播了被毛泽东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将斗争目标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全国各高校很快被“发动”起来。仅仅第二日,卞仲耘和她领导的班子,也成了女附中红卫兵的“革命对象”,并开始遭汹涌的大字报围攻、批判与漫骂。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全国大、中、小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由此运动继续被引向深入,斗争很快升级,这使原本在北师大女附中处于统治地位、足以呼风唤雨的卞仲耘,不仅失去自由,也开始遭受红卫兵丧心病狂的“武斗”。
十几岁的女孩子平时也许弱不经风,一旦被“发动”起来,穿起军装戴着红袖章,撸起袖管手挥棍棒,杀气腾腾地宣称要“誓死捍卫毛主席”,那架势令人不寒而栗。教师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们不仅被戴着高帽子游街、下跪,或“坐喷气式”,被打翻在地时红卫兵小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什么样的“一只脚”?这是穿着厚皮军靴的“脚”,这种厚皮军靴也只有曾参与打天下的高干家庭才会有。这个穿着厚皮军靴的“脚”,往往是踏着受害人的头部,或受害人的脖子,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别以为我这是在信口开河,当年真实历史的惨状,我远远无法完整表达。
我至今记得,那段时期内北京曾有一名教师,被一群红卫兵押着在街上游斗。红卫兵手上带钢扣的大皮带不断抽打在他的头上、脸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之下,这名早已伤痕累累、额头淌着鲜血的教师,忽见对面有汽车急驶而来,猛地奋力朝着汽车冲撞,当即惨死于车轮之下,场面血肉模糊、不堪目睹。对这样陷于绝境的自杀者,红卫兵的评价竟是:“态度极不老实”;当年社会上对受害教师的自杀,结论全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卞仲耘死于这一年的8月5日,她死于红色恐怖的罪恶,死于高干子女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一点在今天已无丝毫疑问。8月5日又是一个重要标志性日子,毛泽东在这一天公开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由此宣告刘少奇的死刑。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数万红卫兵,打死卞的主要凶手被推举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打死卞的凶手给予了鼓舞:“要武嘛!”这一基本史实,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无人不知。从此凶手更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也改校名为“红色要武中学”。8月23日起,红色恐怖的暴行开始向全国漫延。8月24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对他的部下告诫:“如果你们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的回答是:“好人打死坏人,是活该;好人打死好人,是误会;打死了就算了,我们根本不用管”。公安部长一席话,标志着一个社会完全进入野蛮、黑暗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卞仲耘的不幸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其中一个原因是卞被人为添加了虚假的教师身份,同时淡化了她作为主宰教师生杀大权的中共基层头目的真实身份。2009年,卞的铜像在北师大实验中学(原女附中)的实验室落成,打死卞的主要凶手则以“太子党”与留美博士的双重身份回国,在卞的铜像面前惺惺作态地默哀、凭吊,并向卞的家属作了轻描淡写的道歉。独立制片人胡杰在记录片《我虽死去》中,也是把卞当成优秀教师加以颂扬与怀念。网上大量关于卞受迫害文字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但没人注意到,文革中那些在底层受到最野蛮残害的教师和他们屈死的阴魂,至今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同时作为中共控制教师思想的学校最高领导卞仲耘,却成了受迫害教师群体的代表。至今只要谈起教师在文革中的悲惨境遇,人们想到的是却是卞仲耘。在我看,这对无数受尽迫害与摧残的教师而言,实在有欠公正。
美国著名华人牧师冯秉承,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在布道视频中冯牧师讲起一件事:北京某中学门房的校工,被怀疑有“历史问题”(可能正因“历史问题”而不许教书,只得当门房工),被红卫兵抓起来批斗、毒打,勒令交待“反动罪行”。这是1966年的冬天,气温约零下20度。被捆绑在操场旗杆的这位校工,遭受的是怎样一种法西斯酷刑呢?红卫兵先将一桶烧到沸点的开水,从他的头顶浇灌而下,紧接着又是一桶近于冰点的冷水浇下去,再接着又是一桶开水……这是一幕丧心病狂、惨绝人寰的迫害,几桶水下去,受害校工头上脸上早已皮骨分离……
这个可怜的受害者,果然是“死了也就算了”。半个多世记过去,除冯牧师在布道时提起外,人们早就忘了受害者曾经作为一个生命而存在的事实。还有上文提及的在街上被游斗、被殴打,只能一头撞向汽车以求解脱的教师,还有无数我们根本不知情的受害教师。互联网上甚至找不到他们的姓名,但他们每人都有自己一段极其惨痛的经历。他们与卞仲耘不同,因为他们在强力专政的铁蹄下,只能属于被唾弃的异类或任人宰割的牲畜;他们的生命如同蝼蚁一样微不足道,人们不可能为他们建造纪念铜像,也不可能有人表示道歉。
当初迫害、毒打他们的凶手,也许早成为呼风唤雨的各级党政领导,或是腰缠万贯、二奶簇拥的官员,或是留洋博士、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之流。大批受害教师的苦难正在被一天天地遗忘,而曾经是中共基层组织中掌控教师思想的主要领导人卞仲耘,却代表全体受尽迫害的教师群体,受到人们在互联网上、在电子媒体上的广泛怀念。这正是麦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上世记指出的“道德错乱”(moral inversion),其中充斥着对无耻与不道德的公然认可。
不要用卞仲耘在遭受太子党的凌辱与毒打时的惨相,去掩盖卞在学校曾享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真实。如果说我对文革中深受灾难的教师怀有10分的同情,那么对卞的同情,充其量仅保留5分。原因在于,卞仲耘并非教师,而是控制教师思想动向的中共基层领导,因而也没有资格代表教师。打死卞仲耘的主要凶手,其父系“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重要成员,被打死的卞仲耘,也是“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重要一员,双方属同一阵营。卞仲耘之死,似乎印证了恶魔史达林的一句话:“死一人是悲剧,死1000万人只是个数字”;卞仲耘之死,完全可归为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正如曾经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同样因受迫害而死,也无法追究任何人的法律责任一样。其中一个道理似乎在于,刘少奇在对其他人的政治迫害中,也从来就不会手软。
卞仲耘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