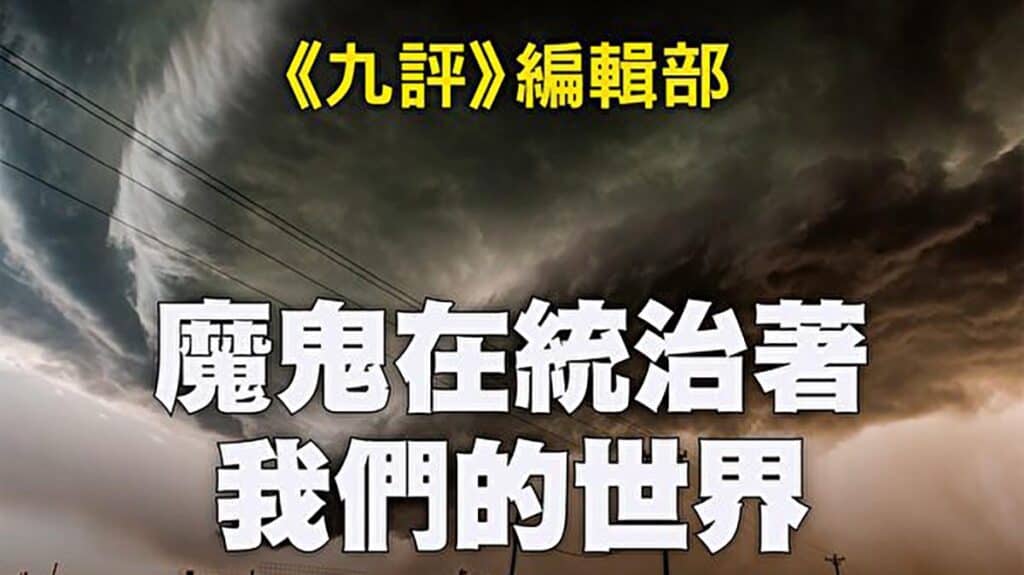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为知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史学界是无人不知。另一位国学大师傅斯年曾评价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共建政后,避居岭南的陈寅恪成为中共当局“招安”的重点人物之一。在毛的提议下,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三个研究所,其中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定为陈寅恪。
委任状下达后,北京多次派人到广州说服陈寅恪,这其中就包括其最得意的弟子、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汪篯,而两人的再次相遇却成为汪篯一生备受诟病之点。
才子汪篯遇到陈寅恪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陈寅恪。在1940年陈寅恪赴英国讲学后,他受到另一位史学家郑天挺的指导,后随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迁到李庄生活了6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硕士论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 与汪篯一同生活在李庄的同学周法高对其的评价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太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汪篯的老师郑天挺对其也持同样的看法。 抗战胜利后,汪篯随史语所回到南京后,并没有留在所里工作,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不久就因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而自行回到北京。当他听说陈寅恪已回清华任教时,遂只身一人来到陈家请求做其助手。出于同情,更是出于惜才爱才,陈寅恪便将其留在家中,让他与另两个助手王永兴、陈庆华共同帮助双目失明的自己教学和研究。王永兴负责和授课有关的工作,陈庆华负责外语,汪篯则负责研究工作。 半年后,经陈寅恪与傅斯年、胡适等人的沟通,北大为了照顾陈的面子,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在两年多的岁月里,汪篯吃住都在陈寅恪家中,与其朝夕相伴。他不仅协助陈著书与修改书稿,而且受益匪浅,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有时他提出的见解,也能为陈寅恪接受和采纳。陈寅恪对其十分满意和喜爱。 也因此,其后,汪篯虽然没有发表太多的论文,但其在中国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一直受到同行的尊重。 投向中共 1948年底,在中共即将进入北平的前夕,陈寅恪仓促南下,而汪篯则选择留在北大。中共建政后,汪篯接受了思想改造,积极向其靠拢,并成为中共所信任之人,还于1952年加入了中共。第二年,又被中共送到北京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马列思想的追随者。 当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汪篯听说中国科学院领导们正在为如何劝说陈寅恪北上而大费脑筋时,一心想向中共表达忠心的他于是主动提出请求,愿意南下充当“使者”,这让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人大为惊喜,遂批准此行。 1953年11月中旬,汪篯怀揣著两封信,一封是郭沫若写的,一封是中科院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行前他放言:“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
师徒两条道路的碰撞
12月1日,汪篯带着两封亲笔信来到陈寅恪家中。此时经中共洗脑后的他,与陈寅恪在对政治、社会的看法上都有了截然不同。或许是自恃自己有“尚方宝剑”,汪篯居然以“党员的口吻”和“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谈话。这让陈寅恪勃然大怒,竟指著汪篯,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之语。汪篯此时才知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此后几天,汪篯一直试图亡羊补牢,但陈寅恪并不能释然。最终,念及当年师生情分,陈寅恪最终答应与汪篯做一次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 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接着,陈寅恪提出自己出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不仅如此,陈寅恪还要求汪篯“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这便是日后学界盛传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显而易见,对于陈寅恪所提的两个条件,中共自然是不会答应。陈寅恪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而与陈寅恪走上了决然相反道路的汪篯,也明白自己与其的师生缘分已尽。同时,因为南下无功而返,且遭到了陈的呵斥,汪篯不仅失去了科教界郭沫若等人的信任,也受到了学术圈的鄙夷。
“反右”劫难与文革中自杀
没过几年,中共发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陈寅恪也在1958年被郭沫若点名批评,而作为其曾经弟子的汪篯地位也一落千丈,遭到批判。汪篯的精神因此受到了极大刺激,大病一场,从一百五六十斤的胖子一下减为不足百斤。 1966年文革爆发,作为文革风暴的中心和策源地的北大,气势汹汹地拉开了“整人”的序幕,而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祭旗的便是汪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们专门在其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据《南渡北归》介绍,第二天,当造反派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篯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 不管是哪个原因,反正愤怒的“小将”见状,开始指责汪篯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 就在当天夜里,汪篯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篯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 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死时汪篯年仅50岁。或许此时的他才明白,只有以死才能抗争这个黑暗的思想不自由的社会。 结语 汪篯死后,被官方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而几年后,他的恩师陈寅恪也被迫害致死。 汪篯的死,开了文革北大教授(教师)自杀的先例。其后自杀的还有: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文教授俞大絪,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生物系教授陈同度,北大教务长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俄语系讲师龚维泰,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和教师陈永和,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 据旅居海外的王友琴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杀或“不正常死亡”。他们或选择服毒,或选择上吊,或选择在未名湖自溺,或选择跳楼……他们死得那么决绝,大概因为人世已不让他们有任何的留恋。 令人叹息的是,迄今北大对这段悲惨、羞耻的一页都不曾进行过反思,而北大的不作为正是中共作为的一个缩影。没有人否认,当中共彻底解体时,所有被中共残害的个体的历史都将被重新掀开──只为历史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