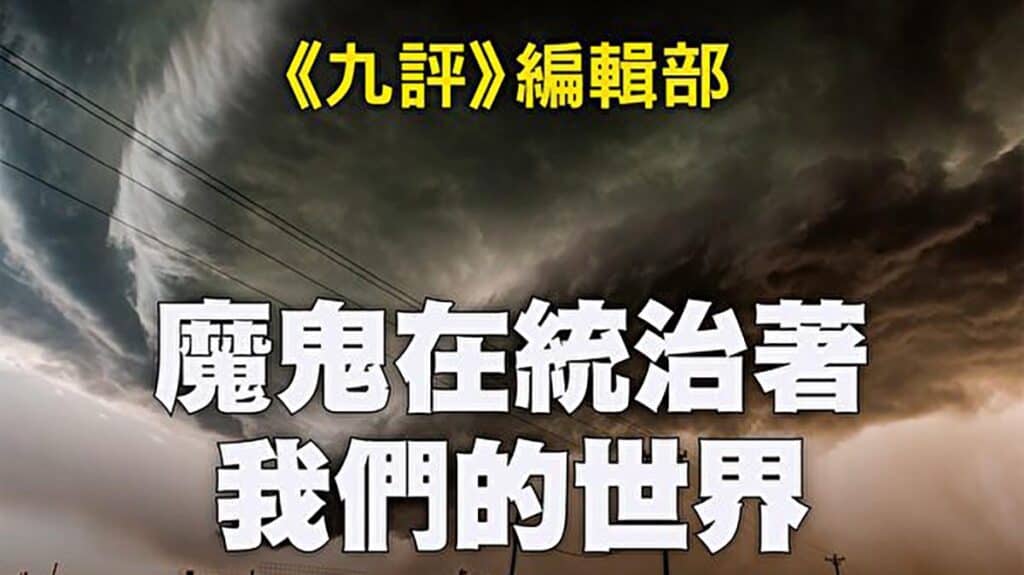在中共关押国民党的战俘营里,有一位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他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书香官宦之家,是中国南宋时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他父亲早年到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相熟,后来还担任过蔡锷的秘书长。
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监狱长要他写悔过书,他说他一直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脱离共产党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当时不走,恐怕早就没有他。
还宣称:“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他叫文强。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却对这个“大哥”终生抱有戒心;他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婚礼,后来却不肯响应周恩来的“归队”召唤;他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同时又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掌权前夕却又退出国民党,留在共产党内;在共产党内出生入死,却不得信任,最后脱离共产党;他被中共一关二十六年半,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却因祸得福躲过了“文革”的劫难。
1930年23岁时成为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比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负责的县都多。当时文强曾经两次被捕逃脱。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婉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文强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断然将文强在被捕期间虚与委蛇应付特务的言行“上纲”判定为“变节”,决定给予处分。罗世文对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还说:“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要清洗”!”这让文强心凉了半截。他早就发现很多党内的同志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里活活淹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他对妻子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
身为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后裔,家族中人无不自幼熟读《正气歌》,“气节”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品德之一。“变节”的罪名自然使他更加无法接受。
文强见要求省委撤销处分无望,愤而决定到上海找中共中央申诉。上海中共中央没找到。而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文强由“变节”升级为“假自首叛徒”,并将他“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了。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其实,文强应该感到庆幸,他仅仅是在中共处于秘密状态的“白区”环境里受到处分……
在中共党内被尊称为“谢老”,时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工农日报》主编的谢觉哉,本已上了自己人的“肃反”处决名单,只因被国民党军俘虏,反倒才幸免于难,谢觉哉后来为此感慨万端地写下了“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的诗句……
因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名句而广为人知的柳是柳直荀,当时的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被中共党自己杀害。
中共颁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所认定的革命烈士,不是被国民党当局或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而是被中共党当成“反革命”杀害的红军将领段德昌……
不同的是,文强在受到中共组织左倾领导人错误处分之后,却在国民党方面感受到了“知遇之恩”。
戴笠约见文强,听他讲了在共产党内的斗争经历,以黄埔同学的名义,力邀其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戴笠就让文强去跟蒋经国上课,因为那时候蒋经国在俄罗斯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对中国的很多情况都不了解了,不管是对国民党、共产党他都不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强已是戴笠手下的军统局高级骨干,当时军统的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文强除了培训,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种情报,他“每天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他还受命花大工夫调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卫参考。上海沦陷之后,他也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搜集到的情报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强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接触过中共的人。在上海马路上,他邂逅了黄埔四期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问他:“你怎么还不归队呀?”并告诉他,周恩来在找他,“在延安给你平反了”。
他问:现在延安是谁主事?袁国平回答:“是毛泽东负责。”
文强说:“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
袁国平说:“你好像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
文强直言不讳:“向来没有信任。”
抗战胜利,文强因抗战有功晋升中将。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文强脱离军统,南下投奔湖南老前辈程潜,在他的绥靖公署当办公厅主任。但很快,杜聿明写信来邀他,又给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调他去当徐州前线总指挥部副总参谋长。
他上了淮海战役前线。文强和几个手下人被包围缴了械。文强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他想“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却被卫士抢了过去。
文强先是在山东关了几个地方,后来被周恩来派人押到北京,关在德胜门功德林模范监狱,编号72号。很长时间他想不通,他的上司杜聿明被定成“乙级战犯”,他反被定成“甲级战犯”! 想不通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关了十多年,1958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
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作为高级战犯关押26年后,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文强后来对儿子们讲述说:“文革”他们这些战犯被集中到大房间,腾出原来的单间来关押新揪出来的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因为仅仅一墙之隔,晚上传来的拷打声、喝斥声,受审者的嚎叫声,以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我是革命的”这样的表白声,不绝于耳,非常恐怖。其他战犯诧异共产党怎么打自己的人这么狠!——文强却一点儿也不惊讶,他在几十年前当中共党员时,早就经历过类似的残酷内斗。
关于“战犯”被改造的生涯,文强在其口述自传中,却一掠而过:上一章末尾写进功德林监狱的情况,下一章开头就是“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近27年春秋成了空白。“无论是什么罪,总有刑期。不明不白被关了那么长时间,他认为是不公正的。”他不愿意再提这段经历。政协却一定要他将在监狱里面27年的情况补充进去,生前出版自传的愿望终成泡影。
与过去的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渐渐了解到,他们虽比他早十多年获释,却比他惨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幸存者也有一箩筐血泪故事。文强对自己最后一批被“特赦”本来十分不满呢,没有想到,监狱竟相当于“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