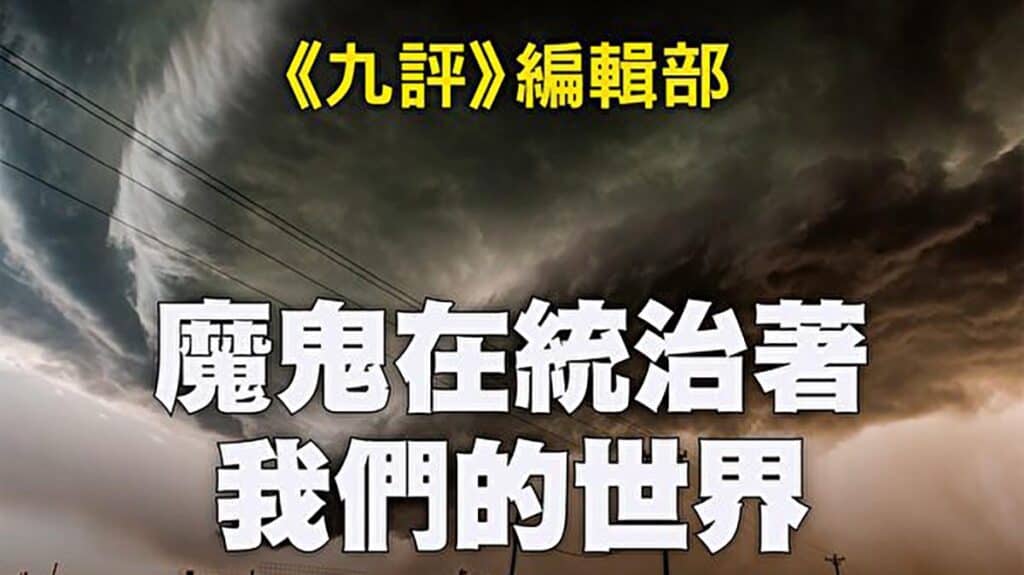2001至2005年期间,笔者在写作《广西文革列传》一书时(2006年11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此书时所用书名为《广西文革痛史钩沉》),曾从《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中引用了多幅照片,使本书增色不少。所有引用的这些照片都是珍贵的史料,其中令人印象最深、最难忘的有三幅照片:一幅是1968年8月1日上午“四二二”派坚守的区展览馆据点被韦国清指使的军队和“联指”派武装攻破后,23名“四二二”派人员被当场枪杀,其余400多人被举着双手,由军人和“联指”武装押送撤离展览馆时的情景(见照片一);另一幅是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在离南宁市革委会不远的民生路“广州照相馆”门前,数名“四二二”派人员已被枪杀,尸体倒在地上,后面是一大批被抓埔的“四二二”派人员,举着双手跪在地上等着枪杀的情景(见照片二),再一幅是1968年7月17日“联指”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致使百货大楼起火燃烧被烧毁后的照片(见照片三)。那时笔者就在想,这些照片太有历史意义了,是南宁围歼、屠杀“四二二”派的历史见证,如能找到当年拍下这些照片的作者、特别是找到那些被抓捕的“四二二”派人员中的幸存者,从他们的口中定会得到许多当年“四二二”惨遭屠城的宝贵史料。
照片一:1968年8月1日上午,“四二二”派的区展览馆据点被攻破后,23人被当场枪杀,其余400多人举着双手被武装押送离开展览馆的情景
照片二: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在离南宁市革委会不远的民生路上“广州照相馆”门前,几名被枪杀者的尸体倒在地上,后面是一大批举著双手跪在地上“四二二”派人员等著被枪杀的情景
照片三:1968年7月17日,“联指”派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派百货大楼开炮,使百货大楼着火烧毁后的情景
从那时起笔者就一直想寻找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和遭受迫害的幸存者,但十多年来始终未能如愿。直到今年的4月中旬,“四二二”派幸存者之一的盛国福先生通过微信给我传来了一份当年南宁屠杀中的一篇文字资料,里面也附有我书中曾引用过的一幅照片(照片二),盛先生发来的资料中说,举著双手跪在地上的高个子是幸存者王xx先生,照片是当年《南宁晚报》的摄影记者甄xx拍摄的。看了这些使我如获至宝,我当即给盛国福先生打电话,问他是否认识王xx和甄xx两人。盛回答说不认识,我又叫他通过当年的“四二二”派人员帮寻找,找到后告诉我,我定要去拜访这些人,以获取更多当年的史料。
恰好2018年4月22日上午有一部分当年“四二二”派的老人要会聚喝早茶,我有幸被邀去参加他们的喝早茶闲聊。在闲聊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明xx先生,他当年也是“四二二”派的观点,同情并支持“四二二”派,反对“联指”派的作法,但他很聪明,从不参予任何一派的活动,在那个年代确是难得的。他还是我的桂林老乡,使我们谈的很投机。在交谈中我拿出了盛国福转来的这份资料给他看,并指著照片上举著双手跪在地上的高个子王xx,问他是否认识此人,明回答说“认识呀!早两天他还同我一起喝早茶,他就住在我家不远,但他曾说过不愿意谈论过去的事了”。
听了明先生之言,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十多年来所要寻找的人终于有结果了。我当即对明先生说:“过两天你安排一下,请王xx先生到你家喝茶,到时我也到你家去,你介绍我与他认识,由我来与他谈有关的问题,至于他愿不愿谈逝去的往事,我们先认识后再说”。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两天后明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一切安排好了,叫我26日上午到他家,具体见面再叙谈。
4月26日上午9时30分我如约到达明先生家,王xx先生早到了,明先生当即给我们引见相识,使我非常高兴。我握著王先生的双手,仔细地打量著,高瘦硬朗的个子,修长的身材,满头白发,虽是同我一样的耄耋老人,但仍显得精神饱满,充满活力。落坐后,我们一边品茶,一边开始了闲聊。我首先作了简要的自我介绍,从文革开始如何回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批资、批修”——等等号召,带领学生参加桂林的“造反”派(被人们习惯性称作“桂林老多”),成了单位“老多”派的头目;其后如何受到镇压迫害,险些丧命,作了简要的自述。接着又说到了此后在长期的野外地质工作中,到过了广西的许多地方,所到之处都听到了文革中的杀人惨案,使我获得了许多广西文革中大屠杀的史料,也使我万分悲痛和愤恨。退休后,我又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从2001年起开始了“广西文革列传”一书的写作——等等,向王先生作了简要的介绍,目的是想引发王先生对往事的回忆。
在我简要地谈了上面这些之后,接着把我写的《广西文革列传》一书展示给明、王两位先生看,并指著书中引用的一幅照片(照片2)对两位说:“当年南宁解放路‘四二二’派据点被攻破后,紧接着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张照片所展示的,前面几个被枪杀者的尸体已倒在地上,后面举著双手跪在地上的人不知是谁,生死如何,令人忧虑——”。“如果我在写作此书时能结识当年更多的‘四二二’派幸存者,定会搜集到更多的宝贵史料,使我的书禸容更丰富、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给世人留下更多的史料”。
此时王先生接过我的话题,大声说:“照片上举著双手跪在地上的高个子就是我呀!我可以说是枪口下余生的幸存者,这段悲惨的历史往事是令人永难忘怀的,至今想来仍叫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唉呀!可找着你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紧握著王先生的手大声说着,“十多年来我都在寻找当年的幸存者,不想今日有幸在此与你相见相识,真乃是天意安排,令我万分高兴”。“你能具体谈谈当年是如何在枪口下余生的往事么?”
早几天明先生曾说王xx先生是不愿再谈往事了的,今天也许是听了我的一番自我介绍,特别是翻阅了我的书和书中所附的照片,显然是对他有所触动,从而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使他终于愿意谈述自己受迫害、差点丧命的往事了。 “照片中被枪杀的死者你认识么?跪在你身旁的人是谁?你是如何在枪口下逃过一劫的呢?”我首先向王先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王先生随口就作出了回答:“前面躺在地上的几名死者,我只认识其中一人,名叫霍普罗,是南宁第四中学的一名青年男教师;跪在我身边的人名叫胡政,其它的我就不认识了”。“至于说我为什么能在枪口下死里逃生,那实在是一种侥幸,一种意想不到的事。当我被强制举著双手跪在地上,‘联指’武装凶手正准备对我开枪的瞬间,此时《南宁晩报》的摄影记者甄xx突然高喊:‘等一下,我把照片拍下再说’。正当他在摆弄相机,调整光圈和距离准备拍照时,一辆军车突然开到急刹车,车上跳下来一名军人,高声叫喊著:‘不准开枪,此人是反动电台的台长,把他打死了,到那里去找口哄’。就这样解放军和那几个举著枪的凶手发生了争论,解放军强行把我们几个押上了汽车,才使我得以在枪口下逃生的”。
“这张照片就是甄xx拍摄的,那时他是《南宁晚报》的摄影记者,我也是该报的编辑记者。文革前我们在一起共事,两人都是三十而立的新闻工作者,比较要好,工作中曾有过图文并茂的友好合作。不曾想文革开始后,特别是自1967年4月起,由于广西军区在群众组织中做‘让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使群众组织中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我参加了反对韦国清的‘四二二’派,甄xx则参加了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自此我们两人分道扬镳,势不两立——。现在我们的据点被他们攻破了,我被他们抓获,落入了‘联指’派凶手们的手中,作为‘联指’派的甄xx,大喜过望的他为了羞辱我,,故而要拍下这张照片以作他们‘胜利’的纪念。谁知我命不该绝,甄xx的此举却意外的硑上了解放军的到来救了我的命,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1983年广西对文革遗留问题进行处理时,甄xx于心不甘,曾情不自愿的向我负荆请罪,赔礼道歉。——尽管他作了这样的表示,但至今我仍不愿与他有任何来往”。
“此后你被押送到何处、给你定了何种罪名、何时被放出来的呢?”紧接着我又向王先生提问。 王先生接着说:“解放军把我押送到看守所,一直关押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时,期间曾遭受过严刑的逼、供、信,诬我是现行‘反革命’,‘打韦、反军’的黑干将,逼迫我承认是‘反共救国团的成员’,也曾被五花大绑、戴高帽、挂黑牌在南宁市区游街示众,受尽侮辱——。其后未经司法审判,就把我送到农场监督劳动,直到1975年才把我从农场放回家中,恢复自由”。“释放回家后,不久对我落实政策,先把我安排到南宁化工厂工作,虽然不如文革前的工作好,但总算是摆脱牢狱之灾了”。
我接着又提问:“你的祖籍地是何处,是何学校毕业,何时参加工作的”。“听说你释放后成了一个优秀的多产作家,很想听你具体地谈谈这些”。 王先生笑着说:“我的祖藉地是安徽,迁居到广西南宁至今已经是第28代了”。“我是1958年南宁四中未毕业就留校工作的,因为那时是大跃进的年代,急需人材,我的学业优秀,就被抽出来当了学校共青团的书记。两年后调入南宁广播电台工作,1962年又调入《南宁晚报》从事编辑记者的工作,直至文革的爆发,此间我的工作都是积极肯干,是很优秀的一员”。“不曾想到1966年爆发了文革运动,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作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而被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险些丧命,这些就无须再赘述了”。
停了一会,王先生又接着说:“我遭到非法迫害前后共有7年多的时间,1975年释放恢复工作后,先到化工厂工作,后到南宁粤剧团任编剧,其后又调到南宁市文联工作。1978年时我写出了小说《彩云归》,是以‘台湾回归’为背景、以统战工作为主题的小说,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此书,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小说奖,此文并被改编成粤剧、话剧在广西和全囯上演,获得好评”。“此后又写了多篇小说,如《汪精卫叛国前后》、《绵绵帝妃情》、《明宫艳史》、《雍正皇帝》、《草莽将军——陆荣廷传奇》、以及杂文集《不认命集》——等等作品,获得过全国通俗文学奖。198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优秀的作家,在此期间并担任了广西区、市的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
“现在我们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王兄你比我年长一岁,你的经历是令我同情和敬佩的。你对过往所走过的路,有何体会与感慨呢”?我又再次提问。 王先生想了想,然后情有所思地说道:“回顾我这一生所走过的路,学生时代是勤奋好学,充满理想的优秀学生。1958年被留校参加工作后,是积极肯干,受到好评的优秀工作者;虽然那时生活较为艰苦,但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工作着想,心情是愉快的。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自己回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运动,结果却惨遭迫害达7年之久,险些丢了性命。这一段经历是我一生最痛苦的岁月,是一段永难忘怀的血泪史,至今想来仍令人心有余悸”。“事实证明,文革是一场浩劫,,特别是在广西,出现了反人类的大屠杀,成了全国文革的重灾区,是历史少见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认识文革,反思文革,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文革之类的灾难永远不会再重演”。
“从上世纪1978年改革开放起,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宽容、宽厚、宽松的环境,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上迅速恢复并高速发展,我的生活安定,工作顺心,使我能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可以说上世纪从1978年起至90年代末,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期,令我留恋、难忘。2000年我退休了,过起了颐养天年的晩年生活,是美好幸福的。当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强盛了,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人是颇为满意的。虽然现在社会腐败,贪腐滋生蔓延,贫富分化悬殊,环境破坏严重,民怨多起——等等社会问题严重存在,但我深信只要坚持打虎反贪,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努力犮展经济,重视文化教育和科技工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前途定会是光明美好的。这是国人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老年人的殷切期望”。
——
听了王先生的上述所言,他的人生遭遇令我同情,他的工作热情和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赞赏和敬佩。非常感谢王先生对我说了这许多宝贵之言,也要感谢明先生,是通过他的安排我才得以和王先生相见、并坦诚交谈的。 是的,王先生说的不错,他的一番感慨令人同情和深思,此次相识并交谈令我获益不少,深受启迪。我很赞同王先生之所言,文革确是一场大浩劫、大灾难,而在广西所发生的灾难更为惨重,不但杀人手段残忍无比,杀人数量更居全国之最,无辜惨死者仅据官方的统计就达9万余人,学者和民间估计至少应在10万人以上,是广西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反人类大屠杀。就以王先生当年所在的解放路琚点来说,包括周边“四二二”派所占据的数条街道,当这些据点被攻破后,竟有1,340人被杀害(包括武斗中战死的数十人),被“俘虏”的“四二二”派人员6,400余人,居民2,500余人,这些被俘者其后许多人遭到了长期的关押、残酷的迫害。造成这样的严重恶果,这个责任当然是文革发动者毛泽东要承担的,林彪和江青的“四人帮”是罪责难逃的;但主要的罪责应该算到韦国清的头上,他是广西1968年出现大武斗及惨绝人寰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只要回顾一下广西文革发展的过程,许多事情就会一日了然的。
据史料所知,文革初期的1966年至1967年的11月以前,广西文革与全国其它地方是大体相似的,并无多大区别。但从1967年11月两派代表在北京经过谈判达成停止武斗,上交武噐,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后,韦国清、伍晋南、广西军区都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中央也同时作出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广西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此时广西的问题理应解决了,社会可以平静,人们也能安宁地生活了,广大人民群众是高兴的。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所料,广西的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越来越糟。从1967年11月起至1968年春,广西一些地方(如玉林、容县、灵山、宜山、荔浦、全州、贺县、钦州、梧州、桂平、鹿寨、罗城——等等许多地方),就不断出现“联指”派围歼“四二二”派的事件,一些地方并出现公开的乱杀人事件(杀地主、冨农和他们的子女,也杀“四二二”派人员),而“区革筹”、广西军区及各地方的军分区、县武装部等政权机关对此则听之任之,不能妥善解决和依法处理好这些事件,使事态不断发展扩大。
在此种形势下,各地受迫害的“四二二””派人员,有的被迫逃到乡下上山躲藏,有的则逃到“四二二”力量较强大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中以求得生存。如果此时的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能站在公正立场上依法正确解决好所出现的问题,广西就绝不会出现后来的大规模武斗,更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凶杀案。因为“联指”派的既定方针是“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而韦国清及军区、各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继续玩弄手婉,仍然在支一派,压一派,把南宁、柳州、桂林诬称为是什么“伍修集团三点一线的最后堡垒”,必欲最后除之而后快。为此,他们一方面向中央谎报军情,诬指南宁、柳州的“四二二”派和桂林“老多”派对他们的批评、抗议是什么“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当这些地方的造反派因受压、受到武装围攻准备武装保卫自己时,被他们诬指为“反革命爆乱”,为此他们就调动农民进诚、甚至公然调动部队协同“联指”武装围歼南宁、柳州及桂林的造反派。更为恶毒的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武力围剿,他们又通过当年的《广西日报》大造镇压“四二二”派的舆论,诬指“四二二”派“杀人放火,搞反革命爆乱”,并别有用心地发出“六·一七”公告,制造“反共救国团”冤案,并胡说“反共救国团”就在“四二二”派据点内,有的“反共救国团成员”成了“四二二”派的头目。他们的这一系列胡作非为就骗取了中央下达“七三布告”,于是他们获得了尚方宝剑,就可以打着落实中央“七三布吿”,打着落实“六一七公告””清查“反共救国团”的旗号,堂而皇之、公开围歼“四二二”派及桂林“老多”派了,终于造成了广西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广西在文革中会出现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事后又长期不作任何处理,让凶手逍遥法外,有的并得到升迁;韦国清和他的继承者乔晓光之流并严禁人们议论文革中杀人之事,谁敢于议论和揭露大屠杀之事,就会被他们以“现行反革命”罪抓捕判刑,如1974年桂林的张雄飞、李新——等等20多人就是因为写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揭露广西各地大屠杀之事,就被非法抓捕判刑,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他们大肆宣扬文革中广西始终有一条“正确路线”,这纯属胡说八道的谎言。要不是那时中央新的领导人胡耀邦等人的英明决策,八十年代初两次派出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调查文革中杀人之事,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开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广西的十多万无辜惨死者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得到平反召雪啊!虽然那时惩办了极少数杀人凶手,追究了少部分凶手的刑事责任,但对大多数杀人凶手则未依法惩处,仅作党纪、政纪问题来处理,就未免处理过宽了,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受害者家属不满意。尽管这样,这样的处理仍是一个历史进步,比之韦国清和乔晓光当政时要好多了。 —— 这段惨痛的历史悲剧虽然过去50年了,但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认真总结、深入反思的。
作于2018年5月中旬
--原载《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