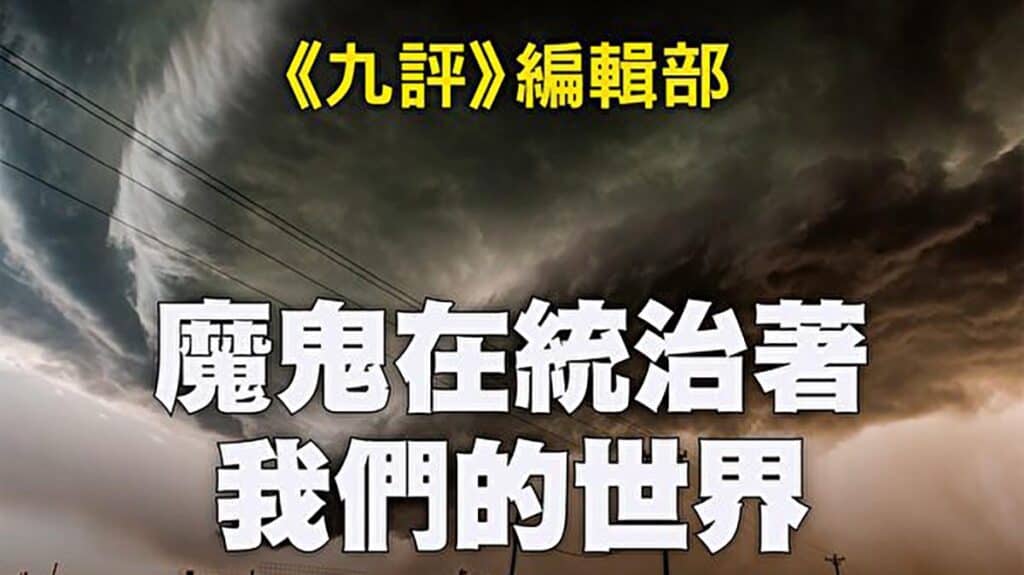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因去北京上访被劳教,二零零二年四月回家后,就被管大院的袁大姐监视起来了:警告、跟踪、监视她都干。我了解到袁大姐“根红苗正”,是市优秀中共党员。文化大革命时,她当中学教师的丈夫被揪斗、关押,红卫兵抄家吓疯了她最小的女儿,为了孩子和自保,她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平反复婚后夫妻关系紧张。
我不记恨她,常常从生活上关心照顾她。出门、回来都跟她打招呼;我家有好吃的也带给她尝;楼道我从上扫到下并常年保持,但每月的楼道清扫费我都如数主动交给她;冬天帮她铲雪;她常年住收发室,土炕返潮腿疼,缺烧柴了,我把不常用的旧家俱劈了送她烧炕;她心脏不好,我给她送水送药。我的真心感动了她,渐渐的她对我有了笑脸,说话也柔和了。但是,当我看到她犯病痛苦的样子告诉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吉言时,她仍瞪起眼吼:“住嘴!想吃苦果子吧”?我不动心,一如既往的待她。
二零零四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她一把将我拽进小屋,小声说:给我讲讲法轮功的事吧,我想听听。从此我经常一边帮她干活一边讲真相。二零零五年新年后,她对我说:“大法真灵,我心不难受了,也有劲了。我也要学大法,李老师,收下我吧,我也要做真善忍的好人。”这时她才告诉我,市“六一零”、公安局、派出所、街道都找她下任务并以看大院的工作要挟,要她盯住我,放线钓鱼。
她笑着说:“他们都知道我是优秀党员,对我可信任了。我就说,放心吧,我黑天白天的盯着她呢,有情况我马上报告。这些年我亲眼看到只有法轮功才是好人。妹子你放心的炼吧,我看着他们呢,我不叫他们上楼去捣乱。”我的眼泪哗的淌了下来,原来她一直暗中不露声色的在保护着我。
二零零五年荷花盛开时节的一天,袁大姐回家吃晚饭,不知怎么被挂到汽车底下,她说:当时也没害怕,还觉著有人把我的手脚并拢,紧贴车轮却没压着。司机要拉我上医院,我不去,又送给我钱,我想起法轮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讹人,我没要。司机和围观的人都说,今天可真遇到好人了。
从前居民往大院扔垃圾她大骂,现在忍不住骂一句马上向师父认错,看到我就像孩子似的喊着:妹子,我又骂人了,我一定改,李老师,我再也不敢了。但劝她退出中共组织,她说还要考虑考虑。
二零零六年,当柳枝轻摇柳絮飞扬的一天,她对我说了如下一席话:我是老党员,我从心里信它,热爱它,我拚命工作,为它争光。……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亲眼看到法轮功和党说的完全不一样,黑白大调个了。要是没有法轮功,我被它骗死还给它唱赞歌呢。现在我看透了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党,它永远再也别想骗得了我了,我连它的一个字都不信了。我三、四年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了,没半句真话。妹子,帮我退!党!!
我望着她背后那颗高大充满活力的柳树说:用“春柳”两字退!党!吧!春天,万物苏醒,柳树又有顽强的生命力。她说,好,就用“春柳”帮我退个干干净净。分手时,她说:我只信法轮功了,跟李老师走到底了。
我久久的望着袁大姐的背影,内心为她的觉醒感到无限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