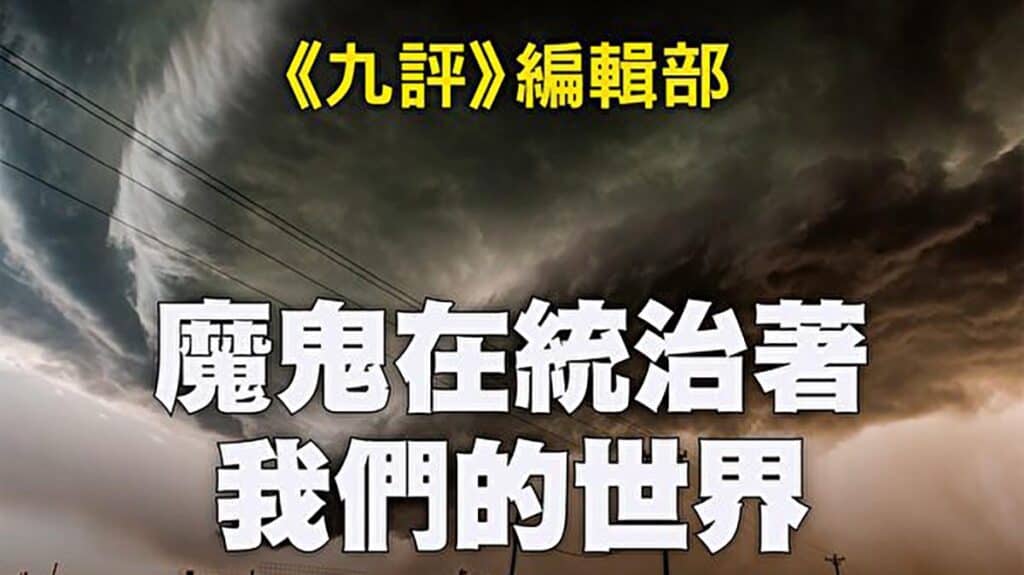凡是读过巫宁坤先生回忆录《一滴泪》的人,对书中描述的“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的受难过程,我想都会留下难忘的印象。
两天前,8月10日,巫先生在美国去世了。尽管人总是要走的,而且巫先生高寿,但听到这个消息,不免还是有些伤感。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江山易色,中共刚刚掌权,真面目还没彻底曝光,尤其对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在它的蛊惑下,当时有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和科学家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梦想,不惜抛弃在国外的学业和前程,纷纷回国。巫先生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回到“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巫先生打算回国前,曾收到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姊姊的严重警告,他们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这阻止不了巫先生的热情,他如期回国。然而,回国后遭遇的一切却是他万万没料到,也不可能料到的。从1951年到1976年,这期间,巫先生经历了三反五反、肃反、“大鸣大放”、反右、文革等一波波政治运动的迫害,可以说几乎九死一生。
而且,遭难的不止是巫先生一人,还有他的家人。
巫先生的女儿巫一毛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她在三岁时随母去清河劳改农场,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小小年纪的她便历经饥饿、贫困、动乱斗争和赤色恐怖。巫一毛幼时寄养在姥姥家,为了让她活命,姥姥以自己的一半口粮哺育她,而姥姥饿坏了身体。巫一毛得过几次重病,求医艰难,几乎濒临死亡。
1966年,文革爆发,巫先生再被抄家烧书,频遭批斗凌辱,羁押牛棚。这年8月,八、九岁的巫一毛自己去医院拔牙,下雨归途中,被一名中共军人用像章诱骗至树林里强奸。还有一次,巫先生在被批斗时,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张定鑫乘人之危,将巫一毛诱骗至家中强奸。
巫一毛在小学时,遭受歧视,屡被欺侮凌辱: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遭揪头发、殴打,遍体鳞伤,甚至昏厥。巫一毛随父母到合肥转学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才得以入学。
巫一毛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年轻守寡,孤身被遣送原籍扬州,宿于祠堂碑屋,因饥饿病痛而死。巫一毛的弟弟在幼儿园被阿姨视为“小贱民”勒令坐在马桶上,不准和小朋友接触。
幸运的是,1980年代,巫先生在历经20多年的苦难后,终于偕夫人和儿女返回美国。在大洋彼岸,当年的极右份子、劳教分子、牛鬼蛇神巫宁坤,终于寻回做人的尊严,施展才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教授。当年的“小右派”、“臭小九”、“狗崽子”巫一毛,也成了美国硅谷计算机公司的高级主管、著名作家。
与巫先生相比,许许多多当年跟他一样,同样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梦想,被中共诱骗回国的的巫宁坤们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大鸣大放”、反右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人相继落难。即使有少数人逃过了这些劫难,到了文革时也无一幸免。
文革期间,在北京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便不寒而栗。几乎所有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统计资料显示,那段时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巫宁坤一家以及许许多多巫宁坤们的悲惨经历告诉了后人一点:千万别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它们许给你的是美好的天堂,但到头来把你拖入的却是万劫不复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