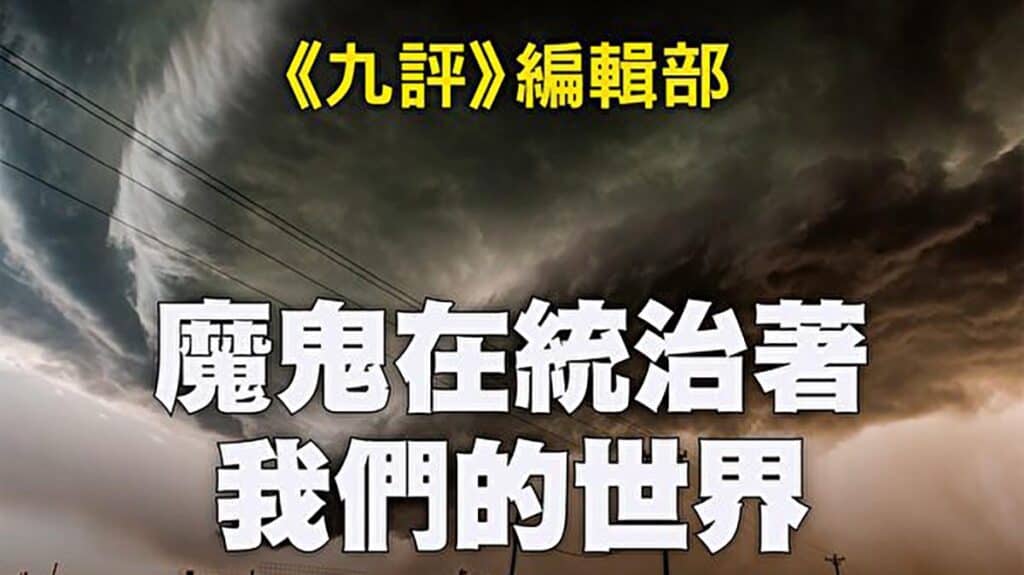著名华裔翻译家巫宁坤,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在美国去世,享年99岁。巫宁坤曾历经三反五反、肃反、“大鸣大放”、反右、文革等中共政治运动迫害,几乎九死一生。
巫宁坤,1920年9月生,江苏扬州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译作有《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并著有中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
他在回忆录《一滴泪》中以“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描述当年受难过程。
巫宁坤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日抗战时期投笔从戎,1943年志愿赴美担任国军轰炸机受训人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留在美国深造。1948年3月,巫宁坤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初尝洗脑滋味
1951年初,巫宁坤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时,突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他尽快回国任教。随后,他也收到中共国务院的信,欢迎他回国工作。
1951年8月中旬回国时,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宁坤也不明白什么洗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回国不到两个月,他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恩来做报告,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他听得头昏脑涨,不禁想到“洗脑子”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吗?
“十一”一过,中共就开始三反、五反运动,12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燕京大学,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当初邀请他的校长陆志韦被大会、小会批斗,就连校长最赏识的副教授吴兴华、陆校长唯一女儿也登台批陆志韦。
紧接着,西语系的巫宁坤也被要求全体师生大会上检讨,刚刚回国才几个月的他想不出自己犯过什么错误,只能深挖自己的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受美国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没料到学生积极分子纷纷指责他平日与学生交谈中言论,以及他把一本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借给了学生,都是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
“思想改造”刚告一段落,教会大学一律停办。于是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巫宁坤因为历史不清,被调到南开大学,被分配教三门课,工作量是全系最大的。他生活也十分清苦,他和母亲被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
肃反运动 成头号“反革命份子”
1955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中共又开始了在学校“肃反运动”,巫宁坤成了学校头号“暗藏的反革命份子”。他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学院的教师大会上被揪出来批斗,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发言,气势汹汹,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四个不速之客就闯入他家。对巫宁坤、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还在家翻箱倒柜,但这个自称公安的人员既找不到“武器”,更找不到“电台”,只得拿走了一些信件、地址本、札记等等。巫宁坤还来不及吃一口午饭就被带到的批斗会,一直批到傍晚。
会上还宣布巫宁坤不得“擅自离校,不得在家接待亲友”。随后,学校不断批斗会,每次会上都要求他交代“罪行”,但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有何罪。
学校开学三周以后才上课。但是,英语专业的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跳水自杀,巫宁坤和另两位教师仍被软禁在家中,所以英语专业停办了。
1956年1月初,妻子李怡楷临产时,巫宁坤因为也不能送她去医院,她只能孤身一人搭公车去市内,当夜生下了大儿子“一丁”。
1956年2月,官媒刊文给知识分子松绑,南开大学的“肃反运动”也收场,天津市委官员也给巫宁坤“道歉”。同年夏天,他被调回北京,在颐和园附近的一所外语学院任教。
反右运动:掉进“阳谋”陷阱
但好景不长,中共又在1957年1月开始了“百花齐放”运动,动员巫宁坤在“鸣放会”上带头发言,给中共提意见,还反复提中共当局制定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政策。
于是巫宁坤提到在“肃反运动”中,他在南开大学遭到无辜迫害的情况,还要求南大党委向他们全家赔礼道歉,但想不到他掉进了“阳谋”的陷阱。他的发言成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他因此被一次次地批斗。
最后,院长还对巫宁坤说,他的“三反罪行”,都可以被枪毙,“现行反革命”,现在他只划为“极右份子”,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1958年4月17日,巫宁坤告别已怀孕七个多月的妻子,被军用吉普车北京市第一监狱内新近开业的劳动教养所,关进二楼的一间监房。监房内关了二十多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两三名,其余大多是“历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
在劳教所四、五十天内,巫宁坤天天被要求“交代罪行”。期间他女儿于6月3日出生。
劳改期间 九死一生
随后,巫宁坤等八百多名“右派”被武警押送到与西伯利亚为邻的兴凯湖国营劳改农场(通称,北大荒)劳动。在那里,他吃了不少苦
1960年10月,农场的三、四百名“右派”全部奉命转移到天津清河劳改农场,离亲人近多了,大家都很高兴。
谁料,三餐改为两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干白菜帮清汤。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浮肿,大便时鲜血淋漓,痛苦呻吟。但即使这样,中共仍然继续强迫他们劳改。
巫宁坤是全中队第一个患浮肿的,再饿下去就要生命垂危了。当时他不忍心向独立一人抚养两个孩子的妻子告急,只能向妹妹等亲人求援。亲人们得信后,火速送来从黑市用高价购买的营养食品,才使他的病情有所缓解。
1961年5月的一天,睡在同一炕上的“右派”死了,一位管教吩咐巫宁坤领三个人到农场一个僻远的角落去埋人。巫宁坤想,“今天我来埋他,谁知道明天睡在我左边的‘右派’会不会来埋我呢?”
于是他就向阔别三年的妻子写信,要她“来见我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她接信后,带儿子一丁来探监。“一见到我活像个饿鬼,她自然惊惶失措,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去北京向学院求情。”
最后妻子的奔走下,一个月后,他被批准“保外求医”。
文革中被迫下跪
1962年,“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巫宁坤也“沾了光”,被分配到安徽大学外语系当“临时工”,月工资六十元,不及原工资三分之一,还没有公费医疗。
1964年7月,巫宁坤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但仍没有恢复工职,继续当临时工,每月加十元工资。
两年之后,中共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巫宁坤再次被迫害。
1966年6月6日深夜,安徽大学两、三千学生倾巢出动,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时,巫宁坤班上的学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冲进他家,把他从床上揪下来,押解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篮球埸批斗。
“几十名教授、讲师都直挺挺地跪在当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节的学生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了下去。”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写道。
从此,巫宁坤被大会批、小会斗、挂牌游街示众,罚款、扣工资等等,更是家常便饭。外语系的“红卫兵”抄家,连他家的自行车都被“抄走”。每月七十元的工资减为十五元“生活费”。
全家老小被株连
巫宁坤全家老小也被株连。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要她检举巫宁坤的罪行。三个孩子经常被同学骂是“小右派!小反革命!”三岁的小儿子,在幼儿园没人理睬,成天孤孤坐在一个墙角,看别的孩子玩乐。八岁的女儿被巫宁坤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要她照着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宁坤!”
巫宁坤七十多岁的老母,被勒令回原藉扬州。“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看着老人家白发苍苍,苦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两年后她因缺医少药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教授们的“牛棚”生活
1967年,包括巫宁坤在内100多名校领导、教授又开始了“牛棚”生活。他们晚上被要求“交代问题”,或在大会上接受批斗,白天每天被迫劳动长达十小时。他们或是拉着满满一皮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农场车水抗旱,苦不堪言。
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劳改场一名姓郑的复员军人突然要求包括巫宁坤在内八名知识分子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每个人肩上一根粗绳子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
八个人一个个汗如雨下,但姓郑的仍然大声吆喝:“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高头大马的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
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睢就是啦。”
巫宁坤赶快跑步去农场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校长抬上车子,而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
到卫生科后,医生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这并不算啥,更加触目惊心的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沉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
但老讲师否认“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姓郑的猛然用拳打他的右眼,《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枴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1969年5月,中共开始“清队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巫宁坤的妻子儿女,也在“下放”之列,而他本人继续关在“牛棚”接受审查。
一年后,巫宁坤被下放到老家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接受再教育”,直到1974年,即文革快结束时,他才有了工作,在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1979年,巫宁坤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并被调到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
1993年,巫宁坤在美国出版以英文写成的《一滴泪》,中共又停发他与妻子李怡楷的退休金,之后辗转定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