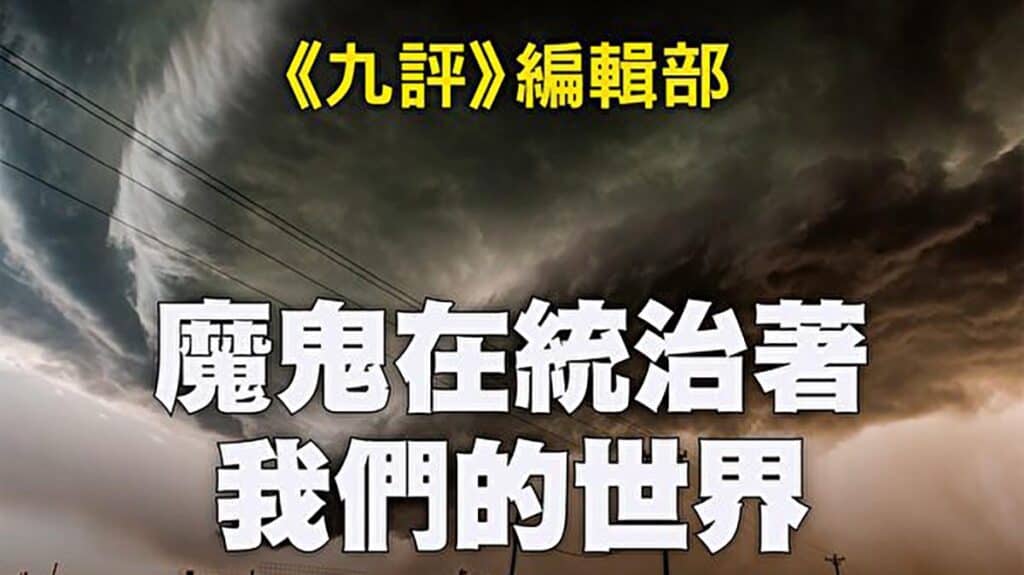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人物专访:遇罗克的家人遇罗文)
上集我们讲到,1968年1月,遇罗克和遇罗文都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他们的母亲被第二次群众专政关在工厂;父亲在营口市,有家不敢回;遇罗锦因为日记问题已经在两年前被判劳动教养;病重的姥姥被二姨夫接走照顾,连家中最小的遇罗勉也被群众专政关在学校。这个家,连续两个多月空无一人。1969年1月,遇罗文被释放回家。此时,遇罗勉已经去陕北农村插队。除了遇罗文从牢房的窗口偶然见过遇罗克一次,姐弟三人再也没有见过自己最亲爱的哥哥遇罗克,想知道遇罗克在监狱中的情况就更困难了。
遇罗克被捕前在1967年12月底家中拍摄的最后的一张照片。(图片来源:遇罗锦博客)
(录音)因为你要知道,监狱里边不能互相的..尤其,我和他一个案子,根本就见不上面,说不上话。后来呢,等我快放的时候呢,碰巧见过几个跟我哥一起关过的,他说(我哥)在监狱里受好多罪,就给他..手背后戴铐子,戴了半年多,生活特别扭,手老在后,让你睡觉的时候胳膊都能搁肿,因为你不习惯嘛,你吃饭啊、什么刷牙啊,什么上厕所都非常难,换衣服几乎都非常难。这个就成天折磨你嘛,让你检举别人,让你承认是自己的错。但他从来没承认,也从来没检举过任何人。确实我知道的不多,张郎郎曾经写篇文章,说得就详细。
遇罗文提到的张郎郎,在文革时因组织文艺沙龙,被判所谓的“思想罪”,一度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张郎郎当年曾经跟遇罗克关在同一个牢房大约半年的时间,后来在死刑号里又碰到了遇罗克。
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遇罗克。(图片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张郎郎出狱后,写了《狱中的遇罗克》、《我所知道的遇罗克》等文章,回忆遇罗克在监狱中的故事。他回忆初次见到遇罗克时说: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他以略带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我叫遇罗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这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的人。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模样。
北京宋庄美术馆郑敏雕刻的遇罗克雕像。(图片来源:遇罗锦博客)
但是,他和其他书生不同,有时候,他还摇头晃脑地吟诵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他的不同还表现在他的胆识,那时候在监狱里的犯人,都要不断的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学习红色革命那套理论,这是一种灌输和洗脑方式。面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时,遇罗克总能做出些不一样的反应。
张郎郎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
当大家背语录背到头昏脑胀时,遇罗克这会儿会突然出奇制胜,激起众人的好奇,说几句招人兴奋的话。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满屋子顿时静下来,全愣了。几个积极份子立刻跳起来抨击他:
“什么?凡是存在的全部合理!那么蒋介石存在,他合理么?刘少奇存在,他也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不着急,继续微笑着说:
“你们仔细想想,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么?” 等批判者的话一级级上纲,到了相当尖锐的时候,他突然就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那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的!”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地笑了起来。
不过,遇罗克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认真。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肯定“门儿清”, 所以,任何人都会在某方面比我知道的多。他在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
遇罗克从小就聪明好学,对各种知识充满好奇,所以即使在监狱中他也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但更大的原因是,当时二十多岁的遇罗克,根本没想到中共会因为一篇文章判他死刑,他还在为自己的未来储备知识。
当然,遇罗克的学识也影响着监狱里的人。张郎郎说他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和遇罗克一起编诗集。他在文章中说:
“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许多犯人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他们似乎隐隐看到,在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浮现出了大漠孤烟、长沟流月的景色。
晚饭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诗词。我对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特有的韵味。只有有了中国文化的根底才能真正理解、体会,也只有用这种形式才能表达中国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也暂时忘掉了铁窗中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