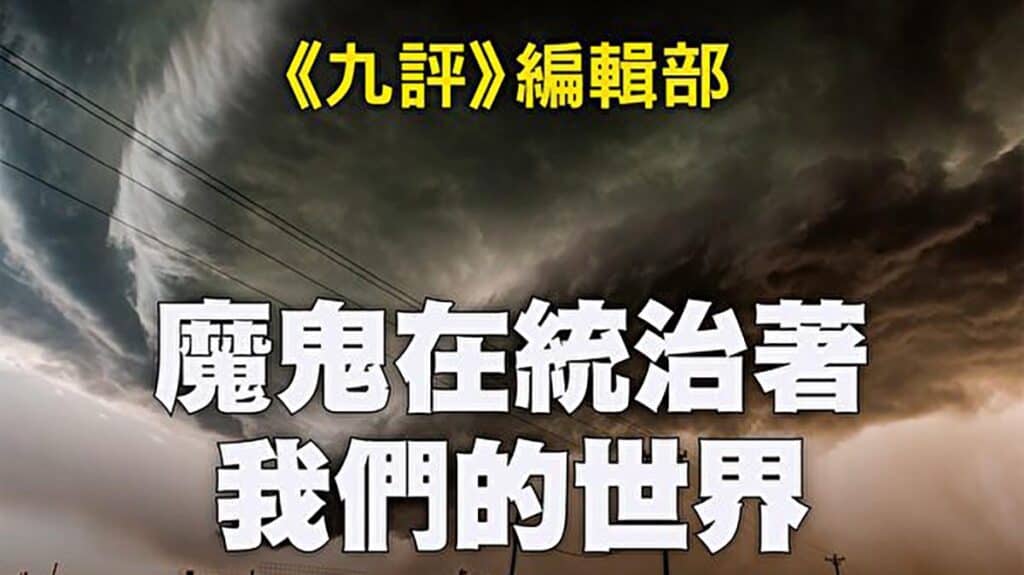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人物专访:遇罗克的家人遇罗文)
上集我们讲到《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在1967年1月18号开始刊印,虽然面对重重压力和阻碍,遇罗文他们坚持了三个月,在全国引起的巨大反响,连办报的人都没有想到—–就在大家齐心协力继续往下干的时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宣布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是“大毒草”,这一天是1967年4月14号。《中学文革报》总共只出了七期,最终在中共的红色恐怖中被迫停刊。1968年1月5号遇罗克被捕,随后与《中学文革报》相关的很多人相继被关押、被判刑。遇罗文和郝治是报纸的骨干成员,他们两人自然是首当其冲。
遇罗文、遇罗勉和父亲在北大荒。(图片来源:遇罗文提供)
“他不说中学生文革报,他不说你办报办错。因为你要说《出身论》不对,那咱们可以辩论辩论,他怎么不对了,那不就把他那个血统论又给抖搂出来了吗?所以他就回避,他说你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我哥这被一关起来后,我呢,他认为我是他成员里边一个,就给我马上去弄群众专政。郝治那个人也非常了不起,他一个大学生嘛,也被群众专政。但我被群众专政还好点,我挨过两回打,都是外校的,都是联动那些人,老红卫兵,他们太坏了,他们我恨的咬牙切齿,但我们学校的人都还好。可这郝治就不行,他们学校的学生太恶了,群众专政嘛,就给他关在楼梯下边的小空间里,每天都要痛打一顿,给他打的非常厉害,打得脸、鼻子、耳朵出血流着呢。打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这么个打法,他就非死不可,他就跟他们说: “今天你们如果再打我,从此以后,我就绝食。”然后这些人哪可能听这个,当然又爆打一顿,他就开始真绝食,他绝食了大约有六、七天,这公安局就害怕了,这公安局本来希望用这个办法让我和他能够检举点事儿,他这一死了,因为他是一个比我还重要的人,因为我可以说我年龄小,什么都不知道,老拿这个推托。但是他的年龄跟我哥一般大,你说不知道,谁信呢,所以怕他死,所以后来才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再打了。等给放出来,一看,他那屋里就搁一草帘,有个枕头,还有一个被,就那么点东西,上面的血都满了,那枕头,都被血结成硬壳了。”
郝治被关押将近一年,这期间他什么都没说,1968年12月31号中共才允许他第一次回家,当天晚上他就去看望了遇罗克的家人。那时一米八的大个子,只剩下90斤。他一进门就对遇罗克的母亲说“如果有坏人跟进来了,您就说正撵我走呢,如果没当场抓住我,只要一出这个门,您就说没见我来过”,所有人都被遇罗克这位硬骨头的朋友感动了。
遇罗文被群众专政时,学校组织过两次批斗他的大会。第一次大会结束后,被几十个联动分子狠狠打了一顿。以后,就把他关在学校。1968年的除夕夜,遇罗文就是在学校一间只有门没有窗的储物间度过的。
新年过后,没多久,遇罗文一位十分要好的同学,经不住恐吓,检举了他从东北武斗地区带回两枚手榴弹的事,学校开了第二次针对遇罗文的批斗大会,之后,立即把他送到了公安局,并关进了监狱。
半步桥监狱的K字楼 如今仅剩下半壁墙和一个墙角的岗楼。(图片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那时候就在这个文革时,我啊曾经从东北武斗区拿了两个手榴弹。我特别喜欢搞武器,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做了所有的炸药,我对武器兴趣特大,我特别想要研究研究这东西是怎么回事,甚至我想给它改进一下。
给我弄群众专政的时候,就想让我说这事儿,但这是我自个儿干的,我就说我哥不知道这事。他们就想办法吓唬我,就给我带到什么看守所呀,说你要不检举的话,你就要升级了,就不是这个群众专政了。他们以为我们同学可能跟郝治他们学校一样,一打,我就害怕了,可他没有想到我在学校里没受什么打。他一看,哎,没什么好办法,就给我开始弄进监狱了。
我一进监狱,就开始老提审,他们特别想让我检举这件事,我还是不说,当然他们不相信。有一次提审的,有一个人在他们里面就是水平最低的,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发誓,要是他知道,判你死刑。”我说,好,他要知道你杀死我都没关系。我看他表情,当时就那么一点头就走了,我估计他这意思是说这回我有了结论。从此以后,再不也不提审我了。”
青年时期的遇罗锦 。(图片来源:遇罗文提供)
可能遇罗文的连死都不怕的坚决态度,让审讯的人相信了手榴弹这件事与遇罗克没有关系,所以不再提审遇罗文。但是在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中,仍然有一条荒诞的罪行:扬言阴谋暗杀。
“最后他没敢说手榴弹,他在判决时没说手榴弹,他就给你加一个扬言阴谋暗杀,但暗杀谁他不说,没有受体那杀谁呢?再说一普通人那也够不上死罪,我无非就扬言,我也没做什么事。扬言就没有阴谋,而且也不说杀谁。现在好多人还跟我纠缠这个,这判决书什么叫扬言阴谋暗杀?这胡平说的有道理,他逻辑性特别强, 他说如果你这手榴弹这事,如果跟毛泽东有关系,他不能够在最后一条,他应该在第一条。你要想杀毛泽东,还不说杀毛泽东,应该说骂毛泽东,你都是死罪,你都要搁在第一条上了。”
虽然不再被提审,遇罗文还是继续被关在监狱里,监狱的生活很艰苦,经常挨饿,他还在这里遇到了很多被长期关押的所谓犯人,他们中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我在监狱待那么长时间,那些犯人都特羡慕,因为这些人关了两年,都不提审,那些人都饿得够呛,都不知道自个儿犯了什么错,都羡慕有个提审,能够表白一下。因为你想,大部份关的都是冤的嘛。
监狱牢房很挤,因为那时候大量抓人嘛,监狱都装不下说实在的,我们睡觉时都只能侧着身睡,因为平躺都不够宽,侧身假如你起来了,你回都回不来。你翻也没法翻身,因为你这一侧挡了你就没法转向了,大部分都是农民,而且关了很长,都关了两三年了,所以每个人都饿得够呛,因为农民本来就饭量大,在这里饭又吃不上。这农民都什么罪过呢?大部份都是四清的时候弄来的所谓四不清干部,他怎么四不清呢?那时候贪污很少,因为那时候人不敢干这事,真正的什么所谓四不清,叫瞒产私分,这个是他们最大罪过。
大伙都经历过粮食困难,都饿得够呛嘛,在分粮的时候,政府规定的又特别少,所以农民想个什么办法呢。农村就用这个斗不用秤,我先邀出一个斗来,这斗假如我邀是三百斤,平的三百斤,可是到真分的时候呢,我都给他装满,给他上尖,这样一来不就比三百斤多了吗?但我名义上记账的时候还写一人一斗,上级来检查我的斗,我可以弄个平的给他邀一下,确实就三百斤。或者比如呢少报地,我把我这生产队的地少说点,这样我打的粮食不就多出一点了吗?多出一点就想办法,那个谷糠,里面参点粮食分给大伙。反正想种种办法,如果没有人检举呢,就没有事。
1970年黄历年前,被警察轰走之前的姐弟三人合影。( 图片来源:遇罗文提供)
到四清的时后就整那些人,让你当众检举,往往谁都有点关关系不好的,那当然就检举了,所以四清是一种很罪恶的运动。四清也整了很多人。只要你替老百姓着想的都得挨着。比如说在粮食困难的时候凡是那横征暴敛,饿死人的基本上没什么事。比如说李井泉啊,包括陶铸啊,都没有降职。凡是同情老百姓的把那个储备粮打开的救济老百姓的,马上免职,甚至给你判刑。还有判死刑的,有的县长还判了死刑。别的官僚看不出来上层什么意思吗?那马上就看出来了。所以对老百姓只能就越来越狠。”
四清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一场思想清洗的政治运动,不少基层干部在这个运动中被整,有人认为,四清运动后来就成了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8年7月, 遇罗文的牢房里又来了一位姓沙的新犯人。
“这个人叫(沙志培)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他是美国公民,他是50年代大概五零年就回中国去、所谓报效祖国去了。他是学法律的,他对中国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主动的回中国,因为他跟周恩来坐过监狱,所以他认为跟周恩来有点交情。可是没想到到了中国以后,中国把法律根本就否定了,律师根本都不用了,也不可能让他当法官。他学法律等于在中国就是没用。他那时候就想求到周恩来能够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务,但周恩来也不帮他忙,他就觉得很失望,所以他就提出了,我想回美国,因为儿子老婆都在美国呢,他本身也是美国公民嘛。可是中国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就没法给他弄回美国了。其实并不是没办法,因为我知道同是在那个年代,到香港去,有的人就可以辗转到美国来。可是呢,当时就因为他可能态度不好,他就跟他们单位领导就吵起来。在当时教养有这么一条,辱骂领导就应该判教养,所以这个领导呢,就以这个为理由给他判三年劳动教养。他到了劳动教养以后呢,就想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放了或怎么着?但是什么都没用。三年到头了,这是该放他了,人当时就问他你有什么要求?我没别的要求!我回美国。就这一个要求!单位说我们没有办法安置这个人,那就接着关、就一直关到了文革我进监狱的时候。你说呆了多少年从50年代初期,一直到60年代,十几年了都。
他给我讲了好多“粮食困难”时经过的事儿。他说,“粮食困难”可苦了。他还好点儿,因为他在粮食困难的时候,他已经算是就业人员了、这就业人员呢,因为他那么大岁数又那么胖,不能干活了,所以他就可以到外面去挖点儿野菜呀逮点小动物啊就靠这个可以充饥。他说其他人,别提多苦了,他说有一次吃鱼,改善生活吃鱼,他不是把鱼刺都吐出来嘛,当时有一个好像鲜族人是教养的人,他说你能把这个鱼刺给我吗?我要吃它。还有这鸡蛋,他们都带皮吃!教养所的、因为太饿了,一点都不愿意扔!可是这老头他没那么饿!他就把皮剥了,别人捡起来就给吃了。有一次给他从这个农场转移到另外一个农场,因为他太胖了,走不动道,就一个人用小推车给他推到、好几十里地呢,给他推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他就问这个人说,给你什么饭吃?这么老远,拉这么累的活!那人说,就给我一个萝卜!临走时发给你一个萝卜这就你的饭!他说那时死人可多了!就饿死的!饥荒年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