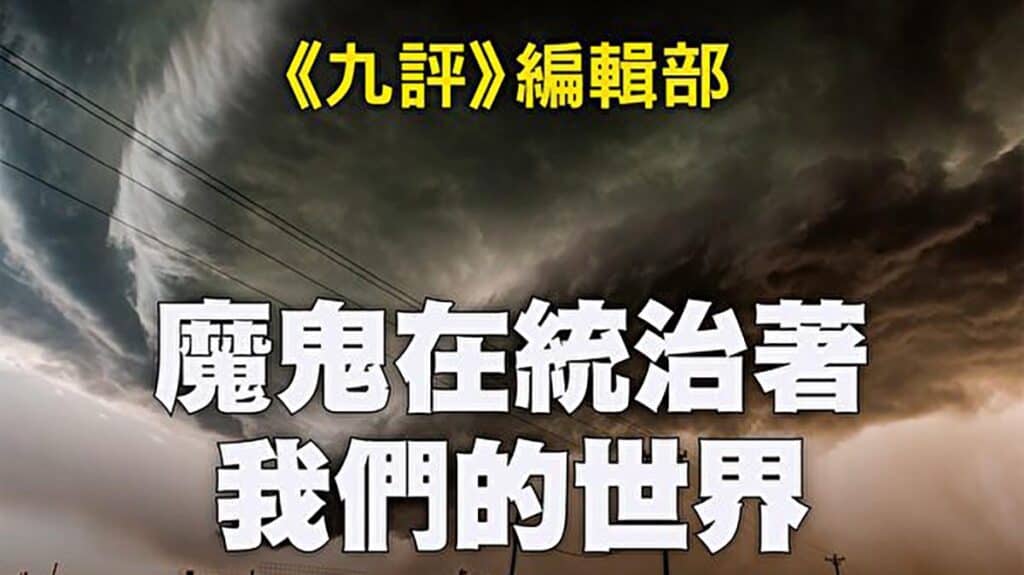回忆“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远无法绕过,此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秉承旗手江青的旨意,所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革”序幕由此拉开,不久无数官员与知识分子厄运降临,但第一个遭开刀祭坛的人物,自然是《海瑞罢官》的作者——集官学于一身的吴晗。吴晗不仅是《海瑞罢官》的作者,还是钦定“三家村”的黑帮分子。
对于厄运突然降临,不仅令吴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轰顶、十分意外,就连吴晗的朋友也感难以理解。要知道1949年后,吴晗曾是为数不多的可出入毛泽东书房的明史专家。
1965年又是吴晗所着《朱元璋传》,在接受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的指示修改后,重新出版的一年。
吴晗的遭遇值得同情。在姚文元奉命拉开“文革”序幕之前,毛泽东已确定的的斗争目标中,吴晗还远远不够格,但为什么要选择先拿下吴晗开第一刀?这可能是毛泽东的战略步骤。先拿吴晗开刀,其实是为敲打1959年在庐山被罢官的彭德怀,而敲打彭德怀,也只是“敲山震虎”而已。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发奇想,提出干部应学习明代海瑞“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的精神。不久,毛泽东的大秘胡乔木将此重要信息转告吴晗,这对于步步紧跟的吴晗而言,正是又一次重要机遇,岂能轻易放过。此后,吴晗接二连三地写出“海瑞的故事”、“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发表在中共顶级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上。
1960年,意犹未尽的吴晗又编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时的吴晗正值春风得意,完全未意识到自已的头颅正钻进一根已悄悄收紧的绞索,甚至连著名京剧艺人马连良,因应吴晗之邀在剧中饰演海瑞,也在1966年惨遭横祸送了老命。
1959年是新中国暴发大饥荒的第一年,吴晗的步步紧跟,其实并非从这一年开始。吴晗的夫人袁震,早就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吴此后的命运也由此决定。在西南联大时期,吴晗就已明确选中紧跟的目标,并以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作为进身的资本。易杜强(美)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版)一书中,称吴晗:“当他(在讲台旁)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同在此书内,作者又指出:“吴晗专攻明史。在他看来,明朝末年,帝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官吏贪脏枉法……,这一切与蒋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吴晗在1949年之前,就已是紧跟红色政权的左翼人士,这在崇尚学术自由与精神独立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多见,除吴晗外还有一人是闻一多。
吴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来带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个时代,文化人由学而官的典范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吴晗。1948年,吴晗由民盟的身份,成为代表新政权掌控北大、清华的接受大员。随着北京和平解放,吴晗又荣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的副手。在以后的几年内,借用岳南在《南渡北归》一书中的点评,吴晗真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950年代前期,吴晗作为权力在握的官方大员,在北京城区的建设规划上,与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发生冲突。梁、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北京老城区传统的文化建筑(包括牌楼、城门等),建议另建新城区,与老城区形成“日月同辉”的格局。建筑学家的良苦用心与真知灼见,彭真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家可能难以理解,但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也不理解,是讲不过去的。
半个世记后的今天,梁、林与吴晗的冲突,已完全毋须再作分析与评论。当年林徽因拖着病躯指着吴晗痛斥,并声明“如果你敢真拆,我就死在这里”时,当事人并没有想到,后人对林徽因产生多么强烈的敬仰,而对吴晗至多也就是不屑了。
1957年的春夏之交,吴晗步步“紧跟”的行为方式更令人深思。在民盟中央面对面批判钦定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的大会上,同为民盟要员的吴晗,作了“我愤怒!我控诉!”的重量级发言。吴晗的批判发言锋芒毕露,声色俱厉句句见血,必欲致章、罗于死地而后快的冷漠与坚定,令人不寒而栗。黄裳先生曾在《读书》上著文回忆此事,文中谈到:
1957年批斗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当年罗隆基要他转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密信,其中有坚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罗的原信是吴晗认为欠妥,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桥疗养院所得。
在关键时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诸于众,并如此横加激烈的鞭鞑批判,吴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赶尽杀绝的坚决态度,比起9年后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对他自己的批判,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朝骨子里看,姚文元其实仅仅是吴晗第二。
吴晗与姚文元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吴晗打击目标所指,全限于知识界;而姚文元的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政府高层(无产阶级的高级干部)。当然这个目标的确定,并不是他们二人自己,他们只是察颜观色、奉命执行而已;二是官方对他们身后的评价也有很大差异——吴晗在“文革”结束后获第一批平反并恢复名誉,而姚文元在此前不久,即被钉在“四人帮”的耻辱柱上。毛泽东去世后的执政者对吴、姚的不同处置,完全与毛泽东相反,此一点同样耐人寻味。
姚文元在1965年的文章对吴晗而言,是丧钟。不久,吴晗遭红卫兵抄家,又被红卫兵绑在树上用皮带抽打,头发被拉光,脖子里被灌入热沙子,鲜血顺裤管流下,之后又被正式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受尽人间地狱的折磨,其妻及一子一女也先后遭迫害致死。而8年前被吴晗往死里整的罗隆基,虽被打成“右派”,却能“死不投降”;虽被撤掉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官职,却有幸未被关押秦城监狱,也没送北大荒劳动改造,更未遭红卫兵的侮辱、批斗和毒打,甚至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还居住在北京乃兹府宽敞的公馆里,还能有老朋友看望、聚会和聊天,甚至聊天中还能大胆表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
1965年12月7日深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平静地离开这个人世,此时正值吴晗的丧钟敲响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吴晗与罗隆基大相径庭的结局,吴晗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吴晗在屈死前,对自己以往为政治而学术的伪学者习气,对自己因“紧跟”而落井下石的种种卑劣行为是否后悔,我们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即如果吴晗没有为“紧跟”而对罗隆基落井下石、没有为“紧跟”而大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与海瑞戏,也不会沦为“文革”一开始即遭开刀祭坛的人物。
在中国,一个读书人绝无可能左右社会制度,个人的行为方式却可由自己选择。吴晗的身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劣迹,吴晗在1957年对“章罗联盟”的残忍杀伐,在一定程度也是对自己的伤害。中国人从前常说的“因果报应”,似乎在吴晗的身上获得验证。
“文革”结束后,吴晗似乎又一次获得回报——除最早获平反及恢复名誉,官方在清华大学近春园的荷塘旁还修建了“晗亭”,这对屈死的冤魂而言,似乎是一种安抚或补偿,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做给活人看的。知识界好像也不甘落后,我所见的文字中,就有人称吴晗的“品质永垂青史”、“人民永远怀念他”,甚至有中年的历史学博士生在文中称之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很显然,如此捕风捉影的廉价赞扬,其实是刻意回避历史的结果。其中真正的原因在于,吴晗的棍子与姚文元的棍子存在明显区别——吴晗的棍子专打在知识分子的身上。在我看来,清华园内的那个“晗亭”,最终将成为对落井下石一类知识分子的嘲讽。
几年前我阅读美藉华裔学者张纯如(Iris Chang)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的“结语”中有一段文字是:
“本书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们遭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进一步的羞辱,并为南京数十万受害者的无名坟墓奉献我写的墓志铭。最终,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本性阴暗面的探索。”这里所谓“人类本性阴暗面”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至令张纯如欲说又止。张纯如自杀前对身边亲友的一句话对此作了解答,她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作为华裔人士的张纯如,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心头也滴着血,但作为学者她又不能不说出真话。我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上世记50年代的吴晗,是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吴晗,是急于自相残害最终又自掘坟墓的吴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的帮助,但却是奴性十足的吴晗。
吴晗的悲哀,不止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悲哀;而对吴晗的赞誉,则显示出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愚昧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