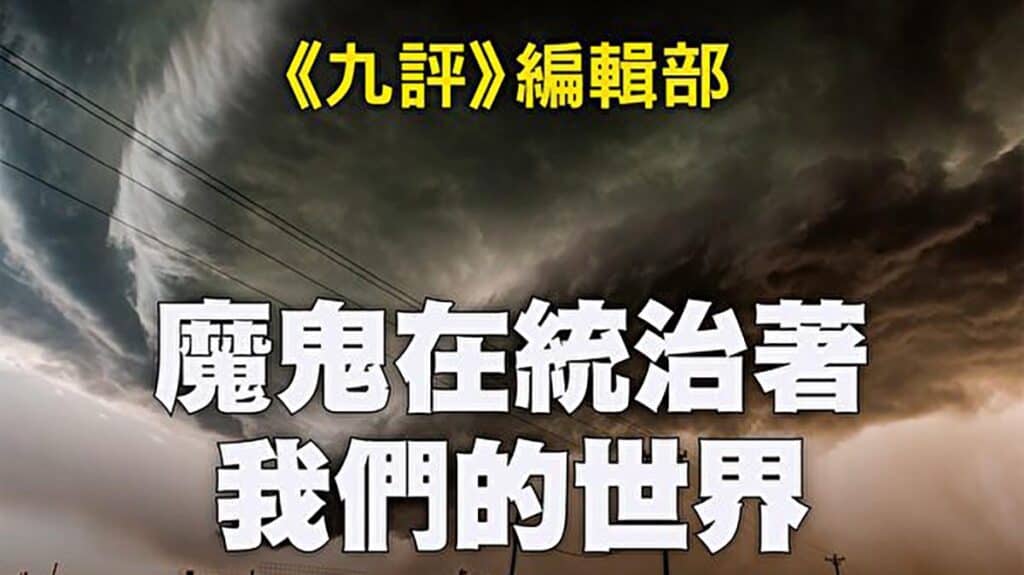1933年我出生在浙江余杭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祖父年轻去世,22岁的祖母抚育繈褓中的父亲长大成家,一个寡妇,艰难哪。父亲是个壮汉,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但好景不长,万恶的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父亲也遭了噩运,31岁离我们去了。从此两代寡妇相依为命,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妹抚育成人。我20岁时被任命为塘栖区完小校长,长辈才有了笑容。只是家庭成分是地主,不能与家里密切接触。妹妹住到了朋友家里,两代长辈理解体谅我们。因为我工作出色,要求进步,当选余杭县第一届人大代表。早已是共青团员的我由区委书记、区宣教委员介绍入党。那是1954年,年底已办理好各项入党手续,只待召开支部会通过。谁料有人密告我寄了40万元(折合现在的币制40元)给家里,说什么“她一只手写入党申请,另一只手给地主母亲寄去大笔的钱”。于是我受团严重警告处分不能入党。1955年元旦,余杭县校长在临平开会,半夜里我冒着大雪,偷偷地到家中探望祖母和母亲,并告知这一切,三个人抱头痛哭。卧病在床的母亲悲愤交加,三天后含怨去世了!临终前叮咛祖母:不能告诉大丫头(指我)。妈妈的有生之年刚到45周岁。
1958年夏,海宁反右运动开始。在领导反复动员、劝导下,我就陷入了“阳谋”之中。有老师们提供材料,让我以漫画形式揭发县委某领导害死两条人命还逍遥法外当他的官。虽然此画引起了轰动,一时群情激愤,纷纷主动签名要求严办凶手。可是不到半天,乌云翻卷,气候突变,我们几个鸣放积极分子被大批大斗,成了极右、一类、二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被降职降薪到最低一级,监督劳动改造。从此送入另一学校做杂工。教导主任周振英,常在师生面前大喊大叫“右派分子就得老老实实!”。当我急性烂尾炎发作时,她竟然硬说我是装死,后幸被校长让人送我去医院治疗。数月后,海宁县的几十名右派全部被遣送东山窑厂监督劳动。那是公安局办的专政机构。除了右派,还有地、富、反、坏分子,有闲散人员,出身成分不好的年轻人,有小偷小摸的孩子,最小的仅9岁。这里没有人权,没有人的尊严,法律在此无容身之地。
进厂后,正值高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放卫星时期,男女老幼高强度劳动,365天不中断,有病也坚持干,粮食限制,吃不饱肚子。我全身浮肿,眼睛似一条缝,闭经,血色素仅5克,可是仍要担负繁重的劳动。我被分配与男性一起抬泥,鞋子磨破了赤脚,开始双脚血迹斑斑,后来磨成老茧反而不痛了。那些孩子敲石子,叫我管着他们,有的孩子会大骂“右派分子不老实”。我忍着,同情他们,他们本应该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啊!在那个可怕的环境里,人还不如一条狗,食堂里的小狗每天吃得摇头摆尾欢蹦乱跳的。
1962年我被勒令下乡劳动,我与李仲华(原是海甯政协委员,在会上发言批评有关领导而划为右派,同在东山窑厂劳改)领了结婚证,回到余杭县东安村我的家乡,与祖母和儿子一起生活。从此离了狼窝又入虎口,四清文革,运动不休,造反抄家,批斗游街,关吊捆打,家常便饭。一年四季手臂上戴个白臂章,黑漆写着“右派”两个字,大门上也写着黑字,早请示晚汇报,常常被拉去义务劳动。我丈夫李仲华在大队丝印社刻版工作,丝印油墨极毒,别人都戴防毒面具,他没有(后来死于右肺萎缩与那时的受虐待有关)。他工作忙,走不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就在他的工分里扣,所谓代“义务劳动工分。”
在文革中我们常常半夜半夜地被拉出去搭台批斗。越斗我越要向上写信申诉,越斗越写,越写越斗,如此恶性循环。造反派大声问:“你再向县里写不写信了?要老老实实交待!”我坚决地说:“放我回去就写!”一阵拳打脚踢打翻在地,治保主任用木棍将我打昏。有一次在公社批斗,被人武部长用枪筒撬碎我的门牙。
最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我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在班主任老师教导下与妈妈划清界线,看着孩子远去的背影,我号啕大哭,伤心欲绝,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是谁夺走了我的儿子?!小儿子英年早逝,遗下我的孙子,还在读书。改正后我做回校长。1987年被选为余杭县第八届人大代表。丈夫李仲华则在余杭双林乡中心小学任教,当工会主席,2001年故世。
往事凄凄,不堪回首……后半夜了,黎明前更加黑暗。思绪犹如万马奔腾,睡意全无,我要挺身去面对更残酷、更惨烈的现实!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