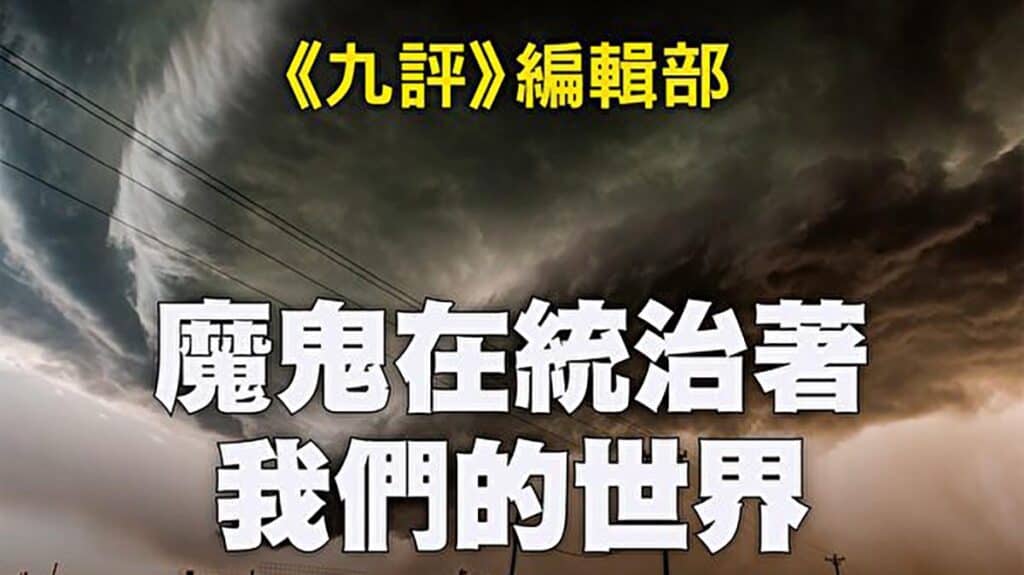1971年秋的一天,邵阳县河伯公社五洞大队第八生产队会计刘义元卖妻的消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且说1968年秋的一天中午,几个手拿梭标、鸟铳的民兵,突然闯进屋高声大叫:“反革命分子刘义元滚出来!”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血气方刚的刘义元听到叫他反革命分子,气得火冒三丈,厉声质问:“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是贫下中农,是生产队会计,谁是反革命?拿证据出来!”“陈良柱就是证据。”刘义元立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刘义元的门。打开一看,是陈良柱跪在他面前,边哭边说:“好兄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虽然出身地主,但哪里也没去过,一直在队上搞生产。你当会计最清楚,一年到头我没缺一天工,未偷一回懒。有人说我参加黑杀队,这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承认,他们就把我吊半边猪,逼我交代。人总要讲天理良心,没那回事,我拿什么交代?不说又要吊。承认是死,不承认也是死,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走,可是逃到哪里去?到处在抓黑杀队,天下老鸦一般黑。你是个好人,请你设法救我一命。我永世不忘!”
刘义元是个有初中文化的人,又是生产队干部,想到利用法律来保护他。陈在刘家躲了两天两夜之后,刘便对他说:“在我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什么办法?”“投案自首。”“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刘义元分析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除了县公安局,谁也救不了你。你唯一的活路就是跑到县公安局,就说自己是黑杀队,特来投案自首。他们就会把你关押起来,你就安全了。”陈良柱觉得有道理,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
当晚下半夜,刘义元站岗放哨。在刘的保护下,陈悄悄溜出大队,迅速向县城塘渡口而去。第二天清早,找到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自报投案。军管小组经查问,知道他是出来逃命的,无法关押,只好把正在县里参加会议的五洞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云松叫来。李马上挂电话让队里快来接人。就这样,陈良柱又被前几天折磨他的凶神恶煞抓回去了,刘义元窝藏陈良柱的事也暴露了。
刘义元驳斥审问他的人:“谁说他陈良柱是反革命?谁说他是黑杀队?真凭实据在哪里?他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我们一同长大,非常了解。他为人老老实实,劳动勤勤恳恳,没有旷过一天工,没有偷过一回懒。他在我家住了两天,我有什么权力把他赶走?你们说他是反革命、黑杀队,请证据拿出来,连人一起送到县公安局去,请政府定罪,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何必你们劳神费心?如果你们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处死人的权力,那么请问: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牌子在哪里?大印在哪里?你们这些人代替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吗?”主审者理屈词穷,怒不可遏。一杯茶的功夫,刘义元即被打晕,耳膜被打破。
刘义元的妻子陈冬青尚在坐月子,千方百计找熟人拉关系,在伤药严重脱销的情况下买了四颗跌打损伤丸,抱着婴儿往公社去给丈夫送药。丈夫头肿得像个西瓜,两口子抱头痛哭。
几天后,一伙横眉怒目、凶神恶煞的人冲到刘义元屋里,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寻找刘义元的反革命罪证。刘义元喜欢读书看报,但又缺钱买不起书,订不起报,因而在外面看到片纸只字,就当宝贝一样捡回来看,碰到一些带韵味的词句,还爱引吭高歌。日积月累,家里集起一堆废旧字纸。搜查者将这字纸全部抄走,仔细查看,终于在一张格子纸上发现几行莫名其妙的字:“日出东来月落西,程度不知路高低。得逍遥处且逍遥,骑驴跨鹤过竹桥。”他们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名堂。就因为这片废纸,刘义元被关进大牢。刘的岳父陈昌顺,原是生产队长,也因陈良柱案被抓,送到县监狱,一年后死于狱中。时年22岁的陈冬青,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挂黑牌戴高帽,游街批斗,被折腾得不像人样,奶水全无,月子里的小女儿饿死在爷爷怀里。
刘义元在牢里一坐就是22个月,进来时是个25岁的精壮劳动力,如今是一天三两米都吃不完,人瘦得皮包骨头,一双膝盖骨一到阴雨天就痛彻骨髓,腰伸不直,腿张不开,头抬不起,身挪不动,比八十岁的老人还差。有关方面怕他死在牢里,又定不了罪,只好放他回生产队接受监督劳动。当他蓬头垢面拄著一根棍子慢慢挪到自家门口时,家里人都认不出来了,夫妻又是一场大哭。
刘义元在监里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出狱后没钱治疗,拖了一年多,病情越来越重。一天晚上,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恐怕活不多久了,现在你又有身孕了。如果我死了,你带着孩子,还有个老爸,生活怎么办?再者,我还顶着个反革命罪名,你就是反革命家属,孩子也是黑五类,长期受欺,永无出头之日。”冬青问:“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做流产?”刘义元解释说:“我是想给你母子找条活路,找一个有前途的人家!”冬青坚决不同意:“我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况且我还怀着你的骨肉!”
在参加完一次四类分子会后,刘义元又乘机试图说服妻子:“冬青,我俩离婚吧,我不能老让你背这个反革命家属的臭包袱。你是贫下中农出身,离了婚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大摇大摆走路,谁也不敢再对你怎么样。”冬青最终同意离婚,但“离婚后我仍住在家里,不能把我赶出去”。
婚离了,刘义元开始琢磨著劝妻子改嫁。他说:“昨夜我做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在一起玩耍,不知为什么忽然吵起来了。别人的儿子骂我们的儿子是反革命崽子,要砸死他。儿子哭哭啼啼跑回来问我:‘你是反革命吗?你为什么要当反革命?’我说:‘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有人骂我翻案,用索子把我父子双双捆了起来。我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为你自己的前途和我们未来的孩子着想,你必须忍痛割爱,决心改嫁。”
冬青哭起来,越哭越凶,如生离死别:“你病这么重,爸爸又老了,身边没人照顾,日子怎么过?”刘义元说:“你如果真的关爱我,就向男方提一个条件,要三五百元钱留给我治病。只要病治好了,一切失去的东西都可以挣回来。”这时刘义元已在邻近的新宁县为冬青找到一位大龄青年。这位青年身体健康,长相不错,心地善良,出身也好,只因家穷,一直找不到老婆。冬青无奈,同意了这门亲事,但向男方提出两个条件:一、她已有身孕,孩子生下来带满周岁后让刘义元接回来;二、因欠账要500元还账。男方表示: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只能拿出200元,多了拿不出。最后双方达成了交钱结婚的协定。刘义元双手接过沉甸甸的大钱包时,以为对方搞错了。区区200元,怎么能这么大一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一元两元的块票和角票!拿着这200元钱,住了20天医院,刘义元的病好多了。
一天,有人给送来个好消息:冬青分娩了,是个男孩。刘义元马上向父亲报喜。儿子周岁后的第三天,刘义元去接儿子。见了冬青,尴尬之余,双手合十,千恩万谢:“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冬青悲欢交集。喜的是他身体比原来好多了,悲的是他还是反革命释放犯。谈到接孩子,冬青说:“接回去还是个反革命崽子。再说,儿子尚未断奶,你接回去如何带?”刘义元无以回答。“还是等断奶以后再说吧。”刘义元只好照办,悻悻而归。
刘义元空手回来,老父怀疑冬青变卦了。刘义元心病渐重,旧病复发。这时年关渐近,队里搞年终结算,两父子劳动一年,仅得80元钱,还被扣除60元的杉树钱,仅余20元。父亲从自留山里砍了几蔸杉树回来做棺材,队上却说,反革命家属没有砍树的权力。鉴于砍的是自己栽的树,从宽处理,不批不斗,罚60元钱算了。刘义元不服气,砍自家山上的树为什么要罚款?找大队干部评理,大队干部说:“你是劳改释放犯,你父亲是反革命家属,没有享受社员待遇的资格。”
听了这个话,刘义元好比五雷轰顶,差点昏了过去。凭空被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哪一天才得尽头?以前卖老婆治病想活下去,如今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老婆改嫁了,儿子又抱不回来,治好的病又犯了,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哪有出头之日,不如早死早超生!决心下定,立即到供销社买了一瓶敌敌畏。
年三十晚上,他把从队上分来的两斤腊肉洗净、煮好、切碎,分成两大碗,一碗给父亲,一碗留给自己,说:“爸爸,今天过大年,我娘死得早,父亲又当爹又当娘苦苦把我养大,谁知儿子没有出息,被误栽冤枉当了反革命,坐了几年牢,身体搞垮了,老婆被卖了,孙女饿死了,孙子也接不回来,害得您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实在是对不住。”刘义元泪流满面。
父亲反复安慰他。刘义元则就著昏暗的煤油灯,背着父亲,将敌敌畏倒在自己那碗肉里。老人问:“哪来的农药味?”他说着“没有”,便端起碗狼吞虎咽呷起来。很久未吃肉了,父亲劝他慢一点,别呷出毛病来。胃开始翻腾了,刘义元对父亲说:“爷老子,你要挺住好好过,不要为我伤心。”说着哇的一声,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农药味弥漫一屋子。父亲以为是他胃不好,受不起油晕,扶他上床休息。
刘义元躺在床上,因疲劳过度,一觉睡到第二天响午。他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是农药失效了?还是药量太少了?他走下床来,端起药瓶子就喝,硬是一口气把剩余的敌敌畏全部喝光。谁知药到肚子里翻江倒海一阵之后,又全部呕吐出来了。父亲看出儿子是在寻短路,急得全身发战,不住地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又说:“傻儿子,新年大节,为什么寻短路?你甩手走了,我怎么办?我知道你心里苦,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还年轻,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洗不白的冤!”刘义元没有死成。
一晃又过了五年,1980年10月,邵阳县公安局发了个30号档——《关于刘义元被拘留一案的复查结论》,称对刘“拘捕不当,予以纠正”。日夜盼望的平反书,盼了10年,终于盼来了。刘义元立即拿了这个档去新宁县接孩子。这时儿子已经七岁了,在读小学一年级。尽管妈妈再三说“这是你亲生的爸爸,喊爸爸”,可是孩子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陌生的爸爸,反而说:“我有爸爸,这个老头不认识。”说罢就跑开了。冬青很同情刘义元,让他多住几天,与儿子交流、培养感情。谁知儿子大了,怎么也无法认同。强迫不行,硬带走他也会跑回来的。刘义元满怀希望而来,满腹失望而去,只好另找老婆,想重续香火。可是家里太穷,年轻的不肯来,拖儿带女的又养不起,年龄大没有生养能力的又不想要,找来找去,找了个39岁的寡妇。生活了三四年,孩子连影儿也未见。刘义元只怪自己八字差,命中注定。
刘义元仍然想念嫁出的老婆和儿子。儿子长得十分健壮,和自己青少年时一模一样,可就是不认他这个生身父亲。他曾反问刘义元:“你为什么要把我娘卖了?我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对我又尽了多少做父亲的责任?”刘义元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后来老父也死了,自己身体也一天天地差,人也一天天地老,分了两亩责任田也无力耕种了。带着后讨的老婆南下打工,可是人家嫌他年龄太大,跑了几个城市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回家没有盘费,生活无著,租不起房,住不起家,只好流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
--原载《黑五类忆旧》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