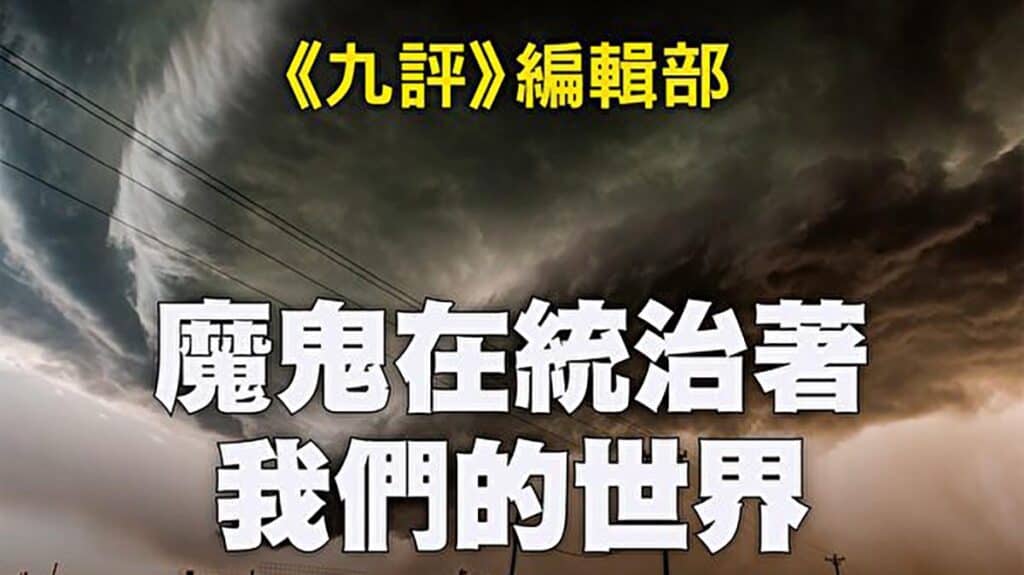前言:由于我的研究理论原稿全部以英文书写(写于2016年),并在欧美部分精英学者里产生很大影响力,我当下认为有必要将我的研究理论翻译成中文,让中文读者也能分享我的理论成果。(欧美非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因此也并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的有色眼镜,而是纯粹以好奇和分析的眼光看待我的研究内容。由于部分学者是专门研究极权主义的,对前苏联和德国纳粹的体制都很熟悉,也非常熟悉著名的研究极权主义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作品,因此看到我的研究非常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也看到了很多新的、独一无二的、既有趣又恐怖的内容。鉴于阿伦特本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部分前言中曾讨论过中国毛时期的反右运动,但由于资料有限未作深入置评,不少学者认为我的研究是对阿伦特理论的极佳补充和当下延伸。)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下软硬兼施干涉全球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导致我的研究不便在学术刊物或主流媒体上刊登。而当下不畏惧来自中国共产党任何压力的,只有《大.纪.元;》。
考虑到在此发表的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普通读者都能读懂我的理论,我在用中文重新书写的过程中将尽可能使用通俗和接地气的语言来阐述学术性的理念和思想,不拘泥于通常写作的条条框框。我也将设法让语言和叙事变得有趣而接地气,随机加入一些发散性内容,多举一些例子来辅助说明不太好理解的概念。
第一章 身体化的集体
核心概念:1.身体化集体 2.罪恶竞争(比谁更坏)3.集体作伪证 4.既是兰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5.逆道德勇气(淫威)6.诡异的“正义”(投票决定谁该倒楣)7.深度冲突(共产党治理理念与独立司法和基本人权理念的水火不容) 台湾学者孙隆基写过一本书非常出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面首次提到中国人“身体化的人格意识”以及以此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人格不独立。孙隆基的直观分析非常准确,但是他将很多华人社群中的某些社会心理学现象归因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设计,有极大的偏颇之处。另有一些非常邪门和恶劣的现象,则是中共大陆一定范围内的专属,并不适用于全球所有华人,也不适用于所有大陆同胞。而他扣的中国文化的帽子着实有点大 – 事实上,49年之后的大陆人往往是最不像历史上的中国人的。但有意思的是,当下偏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在各种宣传管道上表现的最有中国人身份认同。笔者在这里提孙隆基,主要是想向读者说明其“身体化”的概念对笔者“身体化集体”的概念有一定程度上的启发意义,但笔者的“身体化集体”(或者说“身体化极权体”,后者表述更有学术性,而前者表述更直观和顺口)则是研究中共极权主义的理论原创,目的是揭示中共极权主义社会的内在运作机制,与孙隆基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南辕北辙。笔者的英文研究著述中原初使用的是“embodied totality”,然而又觉得embodied不足以表达”身体化“那种直观的动态观感,于是又造了一个新词”bodylized”。因此,身体化集体在我的英文术语中其实是“bodylized totality”或”bodylized totalitarialism” 中共各层党政机关,乃至学校,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小集体构成的。每个小集体里面都有一个身体化的等级序列,构成一个整体化的巨“人”,有人是头(带头的,示范的,或“有头有脸”的),有人是手(打手),有人是腿(跑腿的),有人是背(垫背的),有人是屁股(擦屁股的)。每个人对应的身体部位不一样,其职能也不一样。这里面有着严酷的等级制,并且,越小的集体里面,不同的人的等级和身体部位对应关系越为清晰。而大的集体里面,需要不断的进行例行公事的开会,整风,批斗来让等级关系明了化并重塑有争议的等级关系。中共团体里的身体化等级意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 比如,上级(头)使一个眼色,下级一个跑腿的(民间喜欢称之为“狗腿子”)就会自动跑向一个地方取上级要的东西,心有灵犀而潜移默化。 笔者在此首先叙述一段笔者在大陆中学亲身体验的经历。揭示共产党邪恶的史料和作品非常多,但大多年代稍早。笔者的经历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因此非常具有时代性,对当下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中国大陆所有的全日制公立中小学里都有两样东西,一是“红色教育”(或者叫“爱国教育”,“政治教育”),就是通过课程、展览、视频、宣传等长期反复给学生灌输共产党“伟光正”和阶级敌人的邪恶的;二是“好学生”“坏学生”评选制度。(有些地方是“优等生”,“后进生”,有些地方是“三好学生”,“问题生”等。名词表达会有出入,但万变不离其宗。)笔者所在的中学,学校把基于这两样东西的游戏玩到极致了。 一般的学校都有班干记录学生言行举止的“行书”和评判学生遵守行为规范的“积分制”(比如迟到扣分,拾金不昧加分),这些东西笔者所在学校也都有。但是,诡异的是,“行书”和“积分”都不是在评选“好坏学生”时起决定作用的,仅仅是平时给学生们挠挠痒痒的“走过场戏”。起决定作用的,是周期性的“选举仪式”。 “选举仪式”本身是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事件,因此学校和班主任对此都不会怠慢。在仪式前数周,学校往往狂轰滥炸式的开大会(一开能开几个小时)、开小会、放红色宣传录影、煽动学生极端情绪,其阵势不亚于文革时期武斗前的疯狂造势。而新入级的学生一开始都会不以为然,要么觉得无聊,要么觉得好笑。很多孩子或许在他们父母辈听说过文革的只言片语,但仍然觉得离他们这一辈还挺遥远。不乏有打哈欠的,偷偷做作业的,或小声说笑的 – 这些,班主任都会默默看在眼里,不作声。 经过多日的熏陶,小孩子们有些情绪情感逐渐被煽起来了,冥冥之中仿佛觉得的确有“阶级敌人”“破坏分子”这么一回事,因为再理智的人经过多日的音响录影和会议宣传的熏陶,都会不约而同的在潜意识里打入某种根基。再加上经过几周的磨合,同学们之间基本上也都熟悉了。且新同学认识不久,生活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摩擦和交情。 此时,学校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某日的下午,班主任抽两堂课的时间,专门来做“选举仪式”。 从班主任进入教室的一刻起,学生们就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而严肃的氛围。 “最近我从各门课老师和班干那里都受到一些很不好的回馈”,班主任不紧不慢的腔调反而让全班学生都提高了注意力。接下来几分钟她开始重申一些之前持续数周的“红色造势”中的原则和指导方针,然后又开始谈一些“现实问题”。忽然,她的话锋一转 – “我们这个班集体整体上还是好的,但是就是有极少一小撮坏人在暗中破坏我们这个班集体”。班上此刻已经鸦雀无声,大家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她定了几秒,突然脸色变得狰狞和凶狠,用手狠狠的拍打讲台,并随着拍打的节奏一字一顿吼叫起来 – “他们是谁啊?!”她停止了拍打,但继续吼道 – “我们把他们找出来!” 这个时候,班上已经不仅仅是鸦雀无声这么简单了,大家连呼吸都半憋著,仿佛生怕一丁点吸气的声音都会引发他人的注意。很多人头是低着的,而之前未及时把头低下去的也不敢再把头低下去了,仿佛微微的低头动作都会招致无端的怀疑。怀疑,是的!就是在此时,人与人之间酝酿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此时,班主任反而淡定了。她从讲台里拿出了一叠事先准备好的白纸。 “下面我给大家一人发一张白纸。每个人请把你知道的我们这个集体里的坏人的名字给写上去,写一两个人的名字就行。想好了再写,不要急,写完之后把纸叠起来,我让班干把收上来,我们无记名投票。” 当每个人都拿到那张白纸之后的那几分钟,或许是他们人生至今最难煎熬的几分钟。时间仿佛凝滞了,让人动弹不得。然而,拿笔写字和思考是不可能做到一动不动的,有些学生下意识的抬起头,不经意的对四周打量打量。这时候,当两双眼睛的目光偶然碰触,其结果往往是致命的。猜忌!让人着魔的猜忌! “你眼睛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选我啊?混账东西!你是想害我不成?我懂了!你才是真正的坏人!我就选你,就这么定了!”这样的心理活动,虽然没有人用嘴说出来,但是足可以从某些戏剧般的眼神交流中推断出来。仇恨的种子也就是从此刻开始诞生。而在这种场合,由于有几分钟的“思考”时间,如果一个人一味的埋著头谁也不看,反而又有可能遭致众多不埋头的人的猜忌 – “哦,为什么就他把头总是埋着呢?不会是他心里有鬼吧?说不定他真的是暗中破坏我们班集体的坏人哦?我们就选他好了,说不定他在那里‘阴’我们呢?”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异而恐怖的意识流,而正是这股意识流把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意识给联接起来了。 第二节课是唱票仪式,班主任将无记名的选票公开唱票,并把选中的学生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以画正字的方式一笔一笔记票。由于学校给定的名额是每个班至少摊派两个“坏人”,唱票结束时往往以得票数最多的三至四人为“选举结果”。 被选中的“坏人”除了要写检讨,参加“后进分子培训班”之外,往往还会受到班主任额外的随机处罚,比如罚站,打扫卫生,去后排就坐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班主任往往会纵容同学对“坏人”的霸凌,而“坏人”往往也会因猜忌某些同学暗中投他票而去攻击某人或某些人,从而变成真正的“坏人”。笔者就读的学校,因这种猜忌而发展至私下斗殴并导致重伤的,发生过多起。(笔者离开那所学校后的几年,那里连续发生几起学生跳楼死亡事件,是否与选举仪式有关,无从考证。) 如果说,这种“选举仪式”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让学生措手不及心有余悸的话,那么多次之后,学生们则是“驾轻就熟”了。首次选举,往往会出现选举结果的“正态分布”,意思就是往往很多人都被选中,而得票最多的几个人的得票数量也不会比得票偏多的人多的太多。但是,从第三次选举仪式开始,班主任则不经意的暗示几个学生的名字,称“经班干反映”,或“经某些代课老师反映”,这些学生“有问题”。于是乎,学生们反而大松一口气,开始从班主任给的“暗示名单”中开始“选坏人”了。这个微妙的变化,正是反应了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区别和联系。而此处笔者的经历,正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两者是如何联系和互相转换的。利用极权主义集体中的“多数人的罪恶”,时不时的滴入两滴独裁者意志,那么接下来这个集体会自动地自告奋勇的去竞赛执行这个意志,毛泽东的独裁艺术,也莫过于此。 到了第二学年的时候,班上不仅周期性的“选坏人”,也开始选”模范生“了。但奇怪的是,“模范生”得票最多的往往是班主任已经确立好的班干,而这些班干往往是市里领导的儿子或女儿。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等级制开始在班集体内部形成。一些学生开始跟班干拉关系,平时贿赂和拍马屁,而另一些学生开始主动“教训”跟班干关系不好的人。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宣传中,班主任刻意强调班干的“带头作用”,并警示“排在下面的学生”要小心,不要当“垫底”。这样,一个笔者称之为“身体化集体”的极权主义样板俨然有模有样的形成了。 班干虽然表面上拥有了很大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所欲为,但班干也不可以对班主任目中无人。因为当班主任觉得某个班干“太能了”的时候,往往会在一场临时的班会上“从班干抓起”检讨某些大家面临的问题,让平时被班干压迫的人借机发泄一下不满。当每个人都在与班干们的关系中找到了或被定义在某个等级位置的时候,一个“身体化集体”就准确的确立了。(当然,处在低等级“垫背”或“屁股”上的人,显然是由于不买班干的账而“被定义”的,而处在“胳膊”或“左膀右臂”上的人则是自己在巴结班干的过程中“主动争取”到的自己的位置等级。) 身体化集体的等级架构确立之后,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班主任会在班会上说听说某个人(低等级的)经常迟到或喜欢打架欺负同学,并当场问“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时,超过半数的学生心领神会,会异口同声的说“是!”,(青春期的孩子这么撒谎,倒不完全是邪恶,很大一方面是出于精力过剩恶搞他人的,略带搞笑和团体霸凌的快感,并有“推锅”般的如释重负。但班主任很狡诈很邪恶的利用了这一点,经过特殊的情感把控和挑逗,挑衅,威胁,恫吓,将这种带有恶作剧快感的集体伪证,变为真正的撒谎仪式,并在其后故意伺机让孩子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自愿邪恶”,从而将他们中的一些变为真正邪恶的人。没错,真正的恶人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本来就邪恶并“成为自己”的。) 即便班主任说的事情是子虚乌有。与此同时,班干往往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但这个微笑碰到班主任的目光时会转变成收敛和臣服的表情。(除了班干平时收学生贿赂,班主任平时更是大量接受家长贿赂,有权有势的家长会给班主任开一些权力所及的便利,而有钱的家长会送礼让班主任平时多“罩着”自己孩子。无权无势又不愿意送的家长只能全靠孩子自身的“生存能力”了。)读者不难看出,笔者创造的“集体伪证”的概念正是诞生于此。当一个集体开始撒谎时,无论是主动撒谎还是被动撒谎,多数人已经由被动恐惧迈出了主动作恶的一步。班主任在此用具体的事件来“整人”有一种特殊的用意。读者请注意,当初第一次“选坏人”的时候,班主任并没有指明大家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选,而是泛泛而谈,用之前红色宣传制造的激情和半胁迫式的恐怖来赶鸭子上架。但经过一学年以上的驯化,学生已经形成集体化等级极权体的时候,班主任反而会用具体的“整风专项行动”来驯化心知肚明的奴民面临独裁者指鹿为马时的争先恐后的“集体伪证”。这么做还驯化了孩子们“自己干坏事,让他人来擦屁股”的思维方式,因为班主任往往会借一些整风专项行动选择一些很多人都会犯的小错,比如迟到,上课看课外书,上课偷偷说小话等。而班主任故意针对这些貌似事小的事件,过分渲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制造恐怖,然后让等级排名较后的人来“背锅,擦屁股” – 这样,当多数自己也或多或少有过这些“犯罪行为”的学生来集体伪证只有“经班干提名”的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犯这个罪并试图败坏集体”的时候,多数人心里有一种特殊的快感。甚至,后续很多人还会有意“继续犯罪”,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的罪”将有等级更低的人来擦屁股。同时,他们因巴结班干而产生的屈辱感可以转而借此机会向不巴结班干的“低等人”投射出去。而班主任的狡猾之处还在于,她向拒绝加入等级系统的被迫害者炫耀和卖弄“集体伪证”的狂热时,等于是变相告诉被迫害者 – “看到没有?这可不是我没事跟你有仇哦?这么多同学,绝大多数同学都说是你哦?” 如此,一个身体化集体完美的形成。在这么一个巨人集体中,有人是脸,是头,是眼睛,是嘴(喉舌),也有人是肩膀是胳膊是手(打手)是腿(给头跑腿的)是脚。当然,最不幸运的是做了肛门的。与单纯的比喻不同,笔者这里说的身体化集体是高度准确化和内意识化的,这是中共国很多臣民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比如,作为“腿”的人就是在自我意识里把自己意识为“头”的一条腿,只要“头”一个眼色,立马就向“眼”所望方向奔去(比如取某件物品)。作为“腿”,平时做事不必“要脸”,正如“头”平常想做什么事不必自己“动手动腿”一样。这种现实化真实化的自我意识非常奇妙,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学上的一大奇观。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古已有之,但能做到在一个一个小集体内每个人准确的把自我意识对应到某个他人的身体部位的,却是中共的专利发明。中共利用了中国人古已有之的等级意识,使用现代极权主义体制的独特结构,将人全面锁定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特殊时空内。又由于身体意识是一个人抹去不了的意识(只要一个人还在物理世界里生存的话),中共索性不去做抹掉它的无用功,而是开发渗透一个人的身体意识,在驯化人“集体存在感”的过程中,将集体有意化为一个拥有物理身体的人的符号,并混淆个人对自己身体感知与对这个符号感知的区别。当“我们”取代“我”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时,“我的身体”转而被“我们的身体”或“头的身体”取代优先地位。人的意识已经不是正常的“我意识到我在思考”,或者“我意识到我们在做某事”,而是变成了“我们意识到某个对象”,“我”潜入了身体潜意识,成为了待被意识到的可见可感对象。与一个正常人在想要拿桌子上一杯水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类似,“我们”在想要拿一杯水的时候才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可能就是“我们”的手,但手也可能是其他人,但“我”在意识到“手”是他人的时候,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是“脚”或其他部位。)人的自我意识本来就是有先天缺陷的,以至于很多哲学家在想“我是谁”的问题上常常能进入无限回圈。而德国哲学家康得更是揭示了自我意识“我”的先验幻象。笔者在此且不深入讨论,笔者想表达的重点是,对于自我意识不是很强的人来说,自我意识是很容易被集体意识取代的。中共在军训、过集体生活等过程中渗透了对个体的集体意识训练。而真正在生理心理学上把人驯化成身体化意识的集体的,来源于中共对小孩子早期的“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训练,笔者将在第二章详细叙述。 请注意,班主任平时各种班会使用的语言对还没有意识到“身体化集体”的学生有很有效的引导作用。因为班主任或过于频繁的使用班干要起“带头作用”这样的语言,并且不断的用“垫屁”来恐吓“后进生”,久而久之,哪怕再迟钝的人身体化集体意识也逐渐建立起来了。 在中共的政府、党组织、警察系统里,中小型集体具备的身体化集体对应关系尤为准确,比如某一个中层官员都有固定的“左膀右臂”和“跑腿的”,也有固定的“喉舌”和“打手”再加“笔杆子”(代写稿子的秘书,充当“指头”的作用)。而根据笔者亲身见识,大陆有些法官酒后驾车出车祸的绝不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往往会让秘书来顶包,俗称擦屁股。此时秘书同时充当了“手”和“肛门”的部位作用。而在个别情况下,比如秘书的女朋友也在车上,那么秘书会让女朋友来顶包,此时其女朋友则充当了“肛门”的位置,而秘书本人则继续执行其“手”的职能。 弄懂了身体化集体,也就弄懂了中国大陆。一方面,每一个极权体内部都有一个身体化等级序列 – 当然,在一个集体里,有时候“胳膊”和“腿”不知道哪个等级更高,彼此会有冲突和较劲。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头”的等级一定比“手”高,“脚”的等级一定比”屁股“高。而另一方面,每一个“部位”既扮演着服务于“头”的功能,又与此同时试图发展他的下线,让另一些等级更低的人做他的次级身体部位而自己做“小头”。在这样一个大集体中,一个人可以成为巨人集体的胳膊,而又同时充当某一块“肌肉”(过大的集体中,很多个人是充当大集体身体上某处肌肉的)的“小头”,将那块肌肉意识为自己的手或脚,二次定义两人关系。这么一个古怪的系统是与西方的官僚或公司系统有本质区别的。西方的管理同样有一个层级序列,但这个管理系统的运作是完全依照清晰的规则和法治为依据的。而大陆的这个系统运作没有任何规则,有的话也是达不成共识的潜规则。大陆的系统里,低等级的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高等级的人,并对后者卑躬屈膝。鉴于在极权主义的大陆,权力本身是高度集中的,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利,并往往可以肆意凌辱和虐待下级,因此导致所有人最终都没有尊严。在“共同理想”和“战略目标”面前,每个人都同等多余和没有尊严,而“战略目标”也是说变就变的。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可以被上级凌辱,再把火发泄到下级,因此成为笔者说的“既是兰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兰科夫斯基是二战中有名的迫害自己同胞的犹太官员,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人。) 我们再回到笔者中学的课堂上。在投票时,每个人面临这个邪恶的仪式是必须要做出选择的 – 合作还是抵抗?多数人是选择合作的,少数人选择消极抵抗,比如不按老师和班干的意思选坏人,而是乱写名字甚至写班干本人的名字。但很快这少数人会发现,抵抗是无效的。因为等级排名和排挤低等级的人可以在投票仪式之外悄无声息的进行,以至于投票仪式最终成为走过场,大多数人都写下各位都心知肚明的名单。更严重的是,秘密抵抗的人如果被发现将迅速沦为最低等级的阶级敌人。而班主任如果嗅到了秘密抵抗的人的兆头,会用更加阴险的办法来对付他。在笔者就读的中学,班主任会故意找一些平时有暴力倾向的、头脑不是很发达的学生到办公室谈话,跟他们说某某人跟我举报你们做了什么坏事(这当然是班主任编纂的谎言),这时候这些有暴力倾向的学生便会对某某人恨之入骨,想伺机报复把某某人打死。 这个过程再一次印证了极权主义如何走向独裁主义然后又返回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与独裁主义的显著区别是,后者发生时,到处总是有反抗的。而极权主义发生时,每个人都是自愿参加没有抵抗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在独裁主义社会里,很多人是充满信心有朝一日推翻这个独裁政权的。而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希望本身死掉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抵抗是徒劳的,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什么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