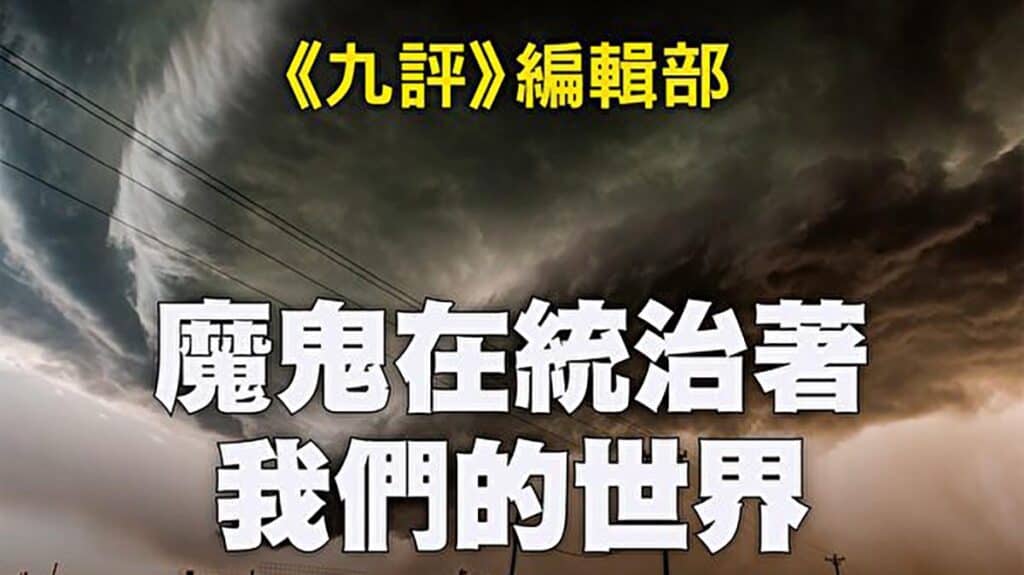我和杨富益都是小学教师,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踏入“阳谋”陷阱,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夏被遣送到新化县吉庆公社监督劳动。我此时才认识了杨富益。他1.7米的个子,身体颇为结实,劳动积极肯干,常挑重担。
我身材略为矮小,且生长在城市,难以承受长期的超强度的劳动和经常的饥饿,就患了全身浮肿病,不能出工,受到了停餐扣饭的惩治。无奈之下,只得请假回家治病。那时,杨富益身体还算健康,天天在队里出工劳动。
几个月后我病情略为好转,回到生产队。此时,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无粮为继,自行垮台解散了。不久,公社为严重的浮肿病人办起了“疗养院”,院里有简单的医药,病人要自带口粮,“疗养院”每天补助一餐大米饭(大米125克),有时还搞点菜枯(菜籽榨油后的枯饼)作营养给病人滋补身子。
杨富益此时身体已十分衰弱,满身浮肿,他先我入住疗养院,因为自带口粮有限,几天以后便出院回生产队了。他“出院”以后我继续在疗养院住了约半个月,疗养院也因物资短缺而解散,我也就“出院”了。
我出“疗养院”回到生产队去看望他。只见他住在一个破旧的仓房内,床是一块木板搭成的,床上只有一床又破又脏的旧棉被,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我见他背倚着墙壁斜坐在地板上,双手放在弯曲的膝盖上,张着嘴,两眼直瞪,僵然不动。我喊了一声“杨富益”,没有回响,我愕然了。
十多天前,杨因断粮在疗养院挨饿,回到生产队后,仍然无粮可吃。他自己一人独住,无亲无故,又是右派,没有人来探问他,关怀他,就这样孤零零的活活饿死了,甚至到底是哪一天死的也搞不清楚了。
发现杨死后的第二天,杨的妻子到生产队来悼念他。他和妻子结婚后不久,就罹难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还没有孩子,就如此悲惨地撒手亡故了,真是断子绝孙,遗憾无穷了。
杨妻到生产队时,队会计对她说:你爱人杨富益还欠队里两斤粮票两块钱。杨妻默然的站在那里没有做声。我见她噙着眼泪极度悲伤,好一会,她才朝丈夫的死处走去。我站在外面,望着杨的住处凝思,依稀听到了杨妻的哭泣声。
我虽然内心十分同情和悲痛,但又无言可去安慰她,只得痴呆呆地站在屋外凭吊。次日,在生产队的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堆。这是生产队的人用杨自己的破脏被和一床破席子包裹着他的尸体草草地埋在那儿了。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想起了杨富益背倚墙壁,双腿弯曲,两手放在膝盖上,张着嘴,两眼直瞪的饿死惨状既使我毛发张起,也使我感慨万千:饿魂遍野的悲惨日子中,自己没有被斗死饿死,留此残身活到今天,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感慨之二是难友杨富益年纪轻轻,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凑数而被划成右派,导致他活活饿死,埋尸荒野,断子绝孙无后代,孤魂野鬼无依托。
联想到当年难友五十五万余人,每个人都有一部辛酸血泪史,每个人都是在“阳谋”的陷阱中挣扎。他们有的被整死、逼死、饿死等等,有的像我一样幸存到今天。但不论已死去的还是幸存者,他们的右派沉冤直到今天仍未彻底洗清,他们付出的血泪代价却仍被“正确的”“必要的”“严重扩大化了”的结论镇锁着。如此不说理,不公正的待遇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纠正!
杨富益饿死已五十年了,相信他的阴魂正在等待着云开雾散的明朗的天!相信所有的被迫害致死的冤魂也同样在盼此明朗的天!相信现代的人都是愿看到沉冤能雪的明朗的天!
--原载:往事微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