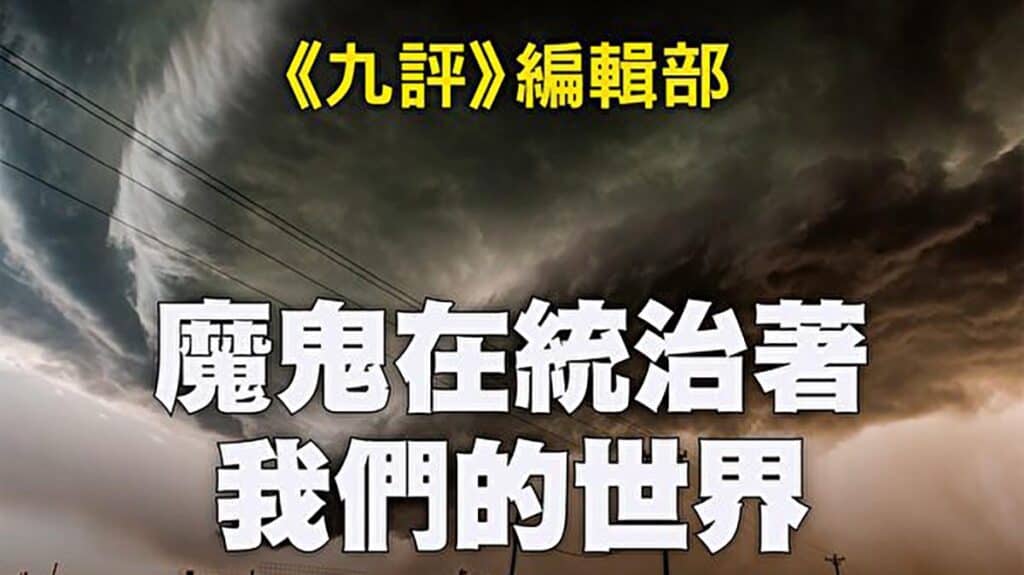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还记当时中国大陆有一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风靡一时,几乎成了青少年们人手一册的必读之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原本是乌克兰人,后加入苏联共党成了一个所谓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该书由他自己口述(因为他当时已双目失明)旁人代书写成,吹嘘他一生的成长经历和所谓的“传奇故事”。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叫保尔.柯察金。一时,保尔成了当时青少年追捧崇拜的对象,比之今天“追星族”们对刘德华或范冰冰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本文中所要说的“钢铁”,却不是保尔那种将人“拟物化”的比喻,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但此物又不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原材料——钢铁。那究竟是什么呢?
1958年毛泽东在食言自肥取得了“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又异想天开,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而发展工业又要“以钢为纲”。于是“他老人家”一拍脑门,便决定要让全国钢产量达到一千零八十万吨。接着,便不顾起码常识,在全国搞“土高炉上马”遍地开花,于是叫炼钢厂大门都未见过,只会种田种地的农民也都来-起大炼钢铁。
此时笔者已由“右派”而升级为“反革命”,并被判刑投入劳改。想不到的是劳改囚徒也“有幸”加入到了这“全民大炼钢铁”的洪流之中。我们从泸州专区监狱被押送到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区岔角滩新生煤铁厂。此地位于川、黔交界的赤水河边,穷山恶水公路也不通。却有无烟煤和铁矿石。由于交通闭塞,煤都只能用船装水运出去。现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来,便把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劳改囚徒驱赶到这儿来,采煤,炼铁。于是乎便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新生煤铁厂”。所谓“新生”,人家的意思是,你们这些右派,反革命是“有罪于人民的”,共产党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故曰“新生”。为此,人家还不知哪里去请了“音乐家”来作词谱曲编成歌,强迫我们每天必须唱,歌曰:“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如此自唱、自骂、自辱,真不知这与绿林好汉把你一身钱财衣物抢光以后,还要你“叩谢大王恩典”有何区别。
再说用来炼铁的土高炉,就是用砖和黄泥巴砌成(当时连水泥也稀如珍宝),外形就象烧砖瓦的窑,不过比它高得多,一面多加个进风口,另面有个出铁口。根本没有什么鼓风机,当时岔角滩,连电也没有,就用铁匠铺里打铁那种风箱来人工鼓风,只是比打铁的风箱大得多,一个人根本拉不动。三个人拉,十来分钟后就气喘吁吁,满身大汗了,就得由另外三个人来换班。如此六个人组成一个鼓风组,一干就是十二小时。但劳改干部真聪明,他们说:“我们工人都上八小时班,你们劳改犯人一天才六小时劳动,你看党和人民政府对你们多么人道主义呀”!他把你工作中换下来松一口气的时间不算上班。有人气得骂道:“这算的是什么账?他妈的混账”!当然只敢背地里骂。接下来便把锤碎了的铁矿石和木炭,无烟煤以及从山上砍下的树木,放在所谓的土高炉里,生起火来就开始了“炼铁”。
但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内行。结果炉内炼成的“铁水”凝成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流也流不出来,只好用钢钎二锤一块块的去敲下来,既不像铁,也不像石头,不知是个什么怪物,令人啼笑皆非。但炼铁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所以后来终于通过上级部门调来了一个技术员。此人姓丁不到四十岁,戴个近视眼镜,大家都叫他丁眼镜,原是重庆钢铁厂的技术员。因为工作中顶撞了苏联专家,反右中又说苏联专家是些不学无术的太上皇,瞎指挥。那年头“反苏,反共”就相当于今天说你要想“颠覆政府”差不多,所以成了右派,反革命判刑10年。经他一番捣鼓,这铁水终于流出来了。于是敲锣打鼓把这块铁抬到厂部去报喜。边走还边唱:“五年计划看三年,苦战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嗨荷嗨菏嗨荷,十五年,十五年,嗨,嗨,十五年!”有个调皮鬼叫王明峰,是个“反革命”和我一样也判刑十五年。一唱到“十五年,十五年”他便用手指一下我,又指一下他自已。他原意不过是要“幽”一“默”,谁知有积极分子去告了密,说他“诬蔑大跃进”,于是乎弄他来斗了几次,以后再不敢“幽默”了。
“大跃进”要的是高产量,而且要天天加码往上升。你那点铁水,根本太少了。上面说这是政治任务,只能完成,否则就是破坏大跃进。新生煤铁厂这时调来一个新厂长叫郑守坤,自称是抗日战争时的老八路,北方人。曾任四川隆昌县公安局长。其人凶恶异常,在这厂内他就像个小暴君,动不动就捆人打人。哪个班未完成出铁的斤两,下班后不许吃饭,睡觉,开斗争会找原因。真是要逼人上吊了。那个技术员丁眼镜确是个好人,他又内行点子多。于是叫人去把什么废铁,烂铁,铁锅,锄头,只要是铁,甚至象铁的废炉渣都弄了来敲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高炉出铁口外砂型内铺得平平整整的,铁水一放出来,那上千度的高温的铁水便把这些废铁烂渣通通凝成一大块,肉眼看上去就是一块新炼成的“铁”,重量就增加了几倍。任务当然完成了。只要完成了产量数目,谁也不来较真。正如现在流行语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丁眼镜后来和我混熟了,知道我也是个右派,反革命,许多观点都和他一样的“反动”。他才悄悄告诉我,这里的铁矿石含铁量太低,根本没有冶炼价值。而且这种土高炉、无烟媒炼出的铁叫“高硫铁”,由于其含硫量太高,根本不能用于炼钢,而且由于其太脆,用来打把锄头,菜刀都要不得,没有任何用处。不如一块石头有用。完全是劳民伤财,白糟蹋资源,乱破坏环境。可是“我党”要和英国,美国比赛,还要“超英赶美”,是政治任务。你敢说半句真话就是反革命破坏!事实证明丁眼镜的话是对的。后来这些高硫铁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堆在铁路两旁没人要,真是不如一块石头有用。但当时就为了炼出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铁”,多少“右派,反革命”活活累死、饿死在这岔角滩的人间地狱——新生煤铁厂了。
在郑守坤这个法西斯暴徒的威逼下,高炉上的囚犯被逼着三天一放“卫星”,五天一放高产。他每天都要亲到高炉上来督阵,他发现谁干活拉风箱不卖力轻则骂,重则打。他甚至把一个他认为“磨洋工,搞破坏”的囚犯捆在高炉旁,当众宣布给“该犯加刑一年”。当时我真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法律。
到了1960年下半年所谓“全民大炼钢铁”终于彻底失败而滑稽谢幕时,这个新生煤铁厂与四川珙县芙蓉煤矿合并。在我离开岔角滩前夕,看见那山坡上一排排无名荒坟不下一百多座。我们这些不幸的朋友(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拿“十五年”来开玩笑的王明峰),他们都在这里彻底得到了“新生”,永远长眠在那没有阶级斗争和政治压迫的天国里了。
而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顶子的郑守坤,万万没想到这“阶级斗争”也终于斗到他老兄头上来了。文革开始,郑守坤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是四川宜宾著名造反派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手下得力的干将,春风得意去北京开个什么会,万万没有想到在北京遇到了他几十年前的一个冤家对头。此人知道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还乡团”的全部历史。他还没认出别人,别人把他认出来了。于是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判刑十五年。大布告贴在宜宾街上。我当时刚出狱不久,正好看见。郑守坤的结局,正如曹雪芹说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由此可见,在极权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遗憾的是那些被他害死在岔角滩的朋友们没能看到这一幕。
2018年10月20日完稿
--原载《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