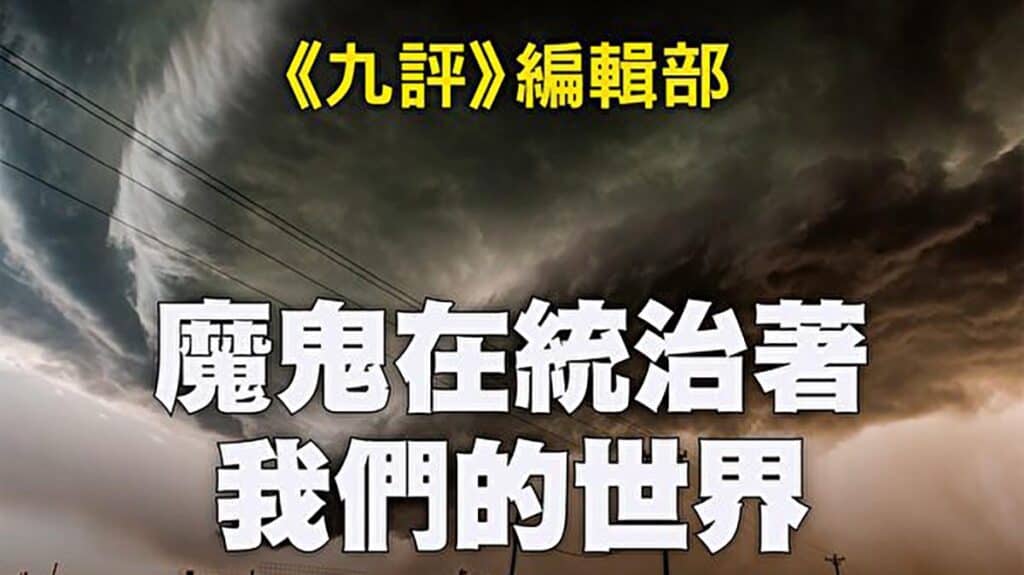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并无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人头攒动、震耳欲聋。人们最喜欢看的游街示众,比北京地坛的庙会还要热闹十分。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著小锣、打着小鼓,没有小锣小鼓的就用旧脸盆、烂簸箕来代替,但是必须要敲得很响。
“牛鬼蛇神”们一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人们欢天喜地围观,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返回来。
人们都拍手笑着、跳着,呼朋唤友地像看西洋景;十分高兴地指点着、议论著:这是谁谁谁,那是谁谁谁。可以说,包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还有看热闹的孩子调皮地泥巴打击“反革命”,一旦头脸被击中,会引起人们一阵阵快意的哄笑。
那些被游者的胸前都挂着大牌子,大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用红笔打着大大的叉。被游者,面孔看上去都差不多,苍白没有血色,目光呆滞无神,如一群羊被驱来赶去。1966年的8月的包头市青山区,我也曾在这样的队伍里行进过,至今想起来,心中仍在滴血。
最壮观的那次是在8月20日,那天,我们都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邱莱走在游街队伍的最前边,他穿着黑色绣花的寿衣,汗如雨下。胸前的牌子上用黑墨醒目地写着:“走资派邱莱”,名字上打着一个血红的叉。
我在最后面,我胸前牌子的名字上也有红叉。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名字被打上红叉,被惊吓哭了,因为听人说过,凡是打上红叉的人,都是要被枪毙的。我呜呜地哭着,脸色惨白,腿也软的迈不开,后来就被两个红卫兵推搡著往前走。
“三反分子”赵华辉和“现行反革命”张亭柱因为悄悄说了一句话,被红卫兵抽出皮带,在他们身上没头没脑地打了几下,就再也不响了。
赵华辉是因为两句话就被打成三反分子的。他那时是食堂的管理员,一天早晨,大家都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老赵突然想起来,食堂没有姜了,于是就喊采购员小王:“今天食堂也无姜了!”就因为无姜,给赵老汉带来了厄运。
还有一次,他在向行政科汇报伙食帐时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又亏了’,下边我公布伙食帐!”行政科长严厉质问他:“你胡说什么,毛主席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指示?”赵胸有成竹地说:“这句话我找了两三天呢!请大家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小资产阶级……发财理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他们每逢年底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不是毛主席说的吗?”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此事后来也成了他歪曲最高指示的罪证。
张亭柱是土建工地实验室的一位试验工,他喜欢文学,因为企图写一本关于北平和平起义的长篇小说而罹难。在小说的初稿里,有人物对话把蒋介石称之为“蒋总统”,他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公司唯一的女“牛鬼蛇神”,子弟小学的乔老师,胸前也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吉普女郎”。她低垂著头,我看不到她的脸,她那美丽的微微带卷的头发已被剪得秃秃的,乱糟糟的匍伏在后脑勺上。我特别想看她那圆润的笑脸,看她那充满智慧的眼睛,但怎么也看不到,只有剪得短短的,沾著泥土的头发在我眼前晃动。
游街常常花样翻新,记得有一次我们还用手牵着一条染成黑色的粗麻绳(寓意“黑帮”)。一路上“打倒×××!”“打倒×××!”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我一个少年,是平生第一次获得“被打倒”的“殊荣”。
有一阵,公司文革小组天天安排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游街。一天,一大早我们就慌忙准备帽子、牌子及手中敲击的响器,主动来到文革小组办公室报到,等待他们派人押解我们游街。后来这些人也烦了,说:“我们没球功夫管你们,你们自己去游吧!”于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就自己打着锣鼓,自己喊著口号去游街。这是什么事啊?所以到了后来,游街几乎成了游戏了,不过这是一个世界上最无聊、最荒唐的游戏。
记得第一次游街用的高帽子是文革小组让焊接队给统一制作的,骨架用的是6毫米粗的钢筋。帽子很重,压在头上,没多久就血脉不通,汗如雨下,濒临绝境。再后来,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文革小组让我们自备道具,于是我们有的用细铁丝,有的用竹篾来绑扎高帽子。我也趁机找来竹篾重新绑扎,细心地用白纸糊好,并写上“三反分子韩丽明”的字样。游街之前,我还在牛棚里对着镜子反复试戴,惟恐出错。有人路过,见此情景不禁哑然失笑。
李总带的超高的高帽也是他自己做的,他说自己的个头小,帽子做的高高才能让大家看到自己。脖子上挂的牌子“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李毅民”的毛笔字也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他的毛笔字很有功底借机会显示显示。
那些很重的铁帽子听说都是焊接队的刘光明焊制的,刘光明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后生,他出身好,对“地富反坏右”深恶痛绝。但是时隔不久,他也被揪出来了,罪名是“侮辱贫下中农”。缘由是,一次大家议论起农村里划成分的事,他说,他们村里就有过地主变成贫农的事情,有个地主子弟因为抽大烟和赌博,到解放前三年已经一文不名,在划成分时竟然成了贫农。在分地主的浮财时,他挑的几件东西,都是当年他赌博输出去的,包括八仙桌、太师椅以及烟枪等,正经贫下中农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看重的都是农具。
刘光明来到牛棚以后,我把替换下来的最重的帽子交给他了。我交给他,让他试戴时,突然想到了一个词:“请君入瓮”。
邱书记是山西人,和我是老乡。在我用竹篾重新做高帽子时,也趁机给他做了一顶,他为此对我感激万分。他说,他老伴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双布鞋,下次再让他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可惜,我没有布鞋,只有工地发的劳保鞋,又硬又硌脚,脚上磨起的水泡始终好不了,后来竟然化脓,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的。
刘光明后来死于自杀,据说由于惊恐而精神分裂。缘由是,包头市要枪毙一批反革命,刘光明被拉去陪绑。那天,他的背上也插着令箭似的亡命牌,活似古装剧中斩立决的牌子。绑得也很有特色,没用手铐,都是用麻绳,从脖子那边套过去,双手反剪,绑的像个粽子。解放军战士背着冲锋枪,两人负责一个犯人,其中一个摁着他的脑袋,让其做出低头认罪的姿势。
他那天被放回来时,脸色灰白,已经肝胆俱裂,没几天就上吊自杀了。
那时,我们每个人上衣口袋处都缝有“××分子”的布条,尽管人不人鬼不鬼,好在都是在工地之内,也就认了。可文革小组有令,出了工地,甚至上大街也得戴着布条走,以便“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我有时候出去只有一个目的,买点儿吃的,补充补充热量,准备接受明天的再一次游街。戴布条走,无异于独自游街示众;不戴吧,又怕躲不过英雄们的“火眼金睛”。思来想去,总算找到一条“万全之策”,我一出406工地就把布条揪下来,回来时再用别针别上去。办法倒是有了,但每次出去都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忽然有一天,公司文革小组的张干事给我们做成四面牌子,牌子上贴着白纸,上面分别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然后命令我们这些“黑帮”们,每天去食堂吃饭时,排成纵队,打头的举著牌子,一路上嘴里还得有节奏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惹得人们都跑来围观。
后来听舅舅说,山西的游街闹得更厉害。听说大同县某公社有个寡妇,是公社书记的姘妇。文革中书记被打成“走资派”,她也被揪出来批斗。因为每次批斗人们都要追根溯源,让她交代与书记的房室之事,具体细节都要求讲述清楚。她不堪忍受,于是上吊自杀。这个寡妇以前曾经是地主的小老婆,人们觉得就这样安葬会便宜了她,不知是谁,想出了裸尸游街的办法。
凝聚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智慧与心血的道具终于光荣诞生了!由木匠定做的坚实稳固的木头架子,固定在一辆牛车上,刘二寡妇赤身裸体地被绑在架子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大活人站立在车上。她的头上戴着高帽,高帽上写着:“大破鞋刘二寡妇”,可胸前却一反常态没有挂牌子,大概设计者是为了突出她胸前那两个干瘪的乳房以吸引人们的眼球。
游街在中国,只是一道旧风景。历史虽说悠久,但真正形成规模和气候的,还应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幼时在老家县城,我曾目睹将罪犯押赴刑场处决的场面,刑车上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杀气腾腾,颇有推出午门问斩的味道。刑车是怎样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死刑犯都是五花大绑,背后插有白色的标子,脸色灰白地站在刑车的最前端。
不过,要是同文革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说文革把人性之恶发掘至极致的话,那么,游街就是不乏幽默、颇具匠心的表演,而裸尸游街更是这种表演中的上乘之作。
唉,难以忘怀的、空前绝后的大革文化命呀,每次想起来就会让我的心上滴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