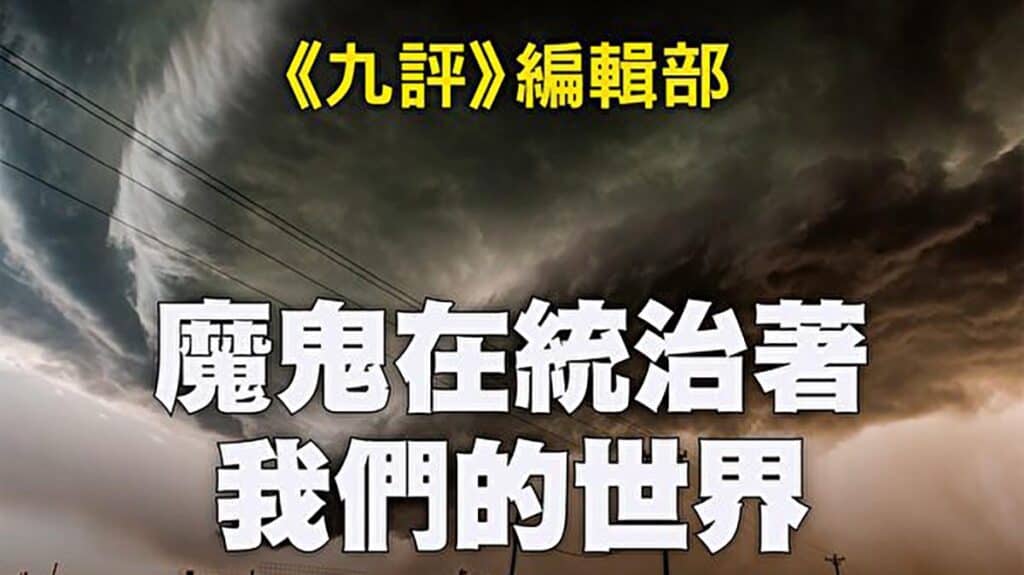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文革”运动是荒唐时代下人为制造的一场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世纪大灾难。这场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他的种种罪孽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国人千秋万代的唾骂。
然而,荒唐时代下爆发的这场“文革”运动,在毛泽东一系列歪理邪说的欺骗和影响下,许多人都会受蒙蔽而被历史的浪潮卷入其中,作出各种不同举动,似乎成了厉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趋势。除去广大普通民众绝大多数人是随大流、被动的巻入运动中而外,其它一些人的表现不尽相同了,在一种错误潮流误导之下,这些人怀着各种不同目的而参予,当中有保守的,有激进的,也有心怀鬼胎的居心叵测者;除此而外也会有少数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作想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反对、抵制“文革”运动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如像湖南的刘凤翔、杨小凯,东北的张志新、史云峰,北京的林昭、遇罗克、王容芬,上海的刘文辉、王申酉、陆洪恩,江西的李久莲、吴晓飞、周海媛……等等中华民族精英之类的人物,他(她)们那种先知先觉、可歌可泣、大无畏的精神和英勇行为,是永远值得国人怀念和崇敬的。
在这里,笔者仅想就文革中那些思想激进的人物,他们在一种错误思潮的指导下,与自身具有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思想构成了某种巧合,从而在文革中会有一种激进的表现,使之一时间成了时代的风云人物,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囗浪尖而备受世人关注。桂林在文革中就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的风云人物,像学生中的周兆祥、李日明、刘振林、谢荣杰、黄沃南、肖社保、梁莲珍、王宋器、吴虹、廖祖亮、唐孟吉,教师中的杨福廷、潘国球、甘恒彩、管学庭、杨正文、蒙木生,韩卓元、林明静,干部职工中的许瑞林、刘天偿、唐兆暄、张雄飞、李新、黄鼎、黄培初、高贵英、赵永强、华天赐、马作刚、郑炳仁、秦玉德、李习炀、饶国强、曾昭炤……等等一大批激进的造反者,通过他们在“文革”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来遭受的迫害和人生之路作某些回顾与探讨,以求对“文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反思,定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杨福廷先生就是这些风云人物中的一位姣姣者,以下是笔者近年来与他多次接触后,通过相互交谈而形成的文字记述,以此作为对桂林“文革”运动的回顾与总结和反思。
一、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
我早就听闻杨福廷先生的大名,那是在1966年的8、9月间,那时位于桂林市独秀峰下的广西师范学院(下称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笵大学)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教师和学生们贴出大字报反对“文革”工作队、炮轰桂林市委、炮轰广西区党委,此事轰动了整个山城,是广西“文革”中最早出现的大事件。杨福廷先生就是这些造反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那时我通过到师院看大字报和该院一些师生的介绍就知道杨福廷其人了。在其后的文革运动中,杨福廷先生都是桂林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桂林市革委会在1968年4月成立时,他是常委之一,是桂林文革中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但我始终未曾有机会与他认识和交往,实为憾事。 时间进入到了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黄培初先生相遇,得知他是我的桂林老乡,文革时也是桂林“老多”派“工总”的负责人之一,自1968年桂林“8‧20”镇压造反派起深受迫害多年,70年代中后期调到南宁工作,现退休在南宁生活。他与杨福廷文革时在桂林就相识,至今仍经常来往,经他的介绍,我才得以结识杨福廷先生,2016年的夏天我与黄培初在桂林第一次拜访了杨先生,至今为止,在桂林和南宁我们已有五次相会面谈,从而对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有了进一步了解,许多事情回忆起来是令人难忘与深思的。 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1936年他出生于广西鹿寨县黄勉乡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在广西师院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他的学习和工作向来是刻苦努力的,对党和毛主席是热爱、忠诚的,只是平时由于对地方官员和社会现实的诸多不满,显得无可耐何,故而对政治上的事不怎么关心。但在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后,却成了一个激进旳造反者,这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给了他造反的机会。毛泽东主持制定的“5‧16通知”,毛的“革命无罪,造返有理”的教导,特别是毛说的“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坻制”,更有毛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和他的其它许多讲话和文章,与杨先生自己具有的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思想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巧合,终于使他走上了激进的造反之路。 文革中杨先生敢于站出来率领师生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当即受到了桂林市委和广西区党委组织工人赤卫队、蒙蔽干部和群众进行围攻,并调动部队出动宣传车企图压制师院学生们的造反运动。然而此时的广西师院多数师生都参加造反派,这就是所谓广西师院的“多数派”,与那时全国许多高校一开始“造反派”都是少数是不一样的,“老多”的名称由此而来,其后桂林市的“造反派”被人们称之为“桂林老多”,此是后话。 广西师院的“造反派”顶住压力,不怕围攻,造反的大字报不但贴在校园内,也敢于贴到大街上,使整个山城为之震惊。8月8日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指出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使师院的师生们深受鼓舞,于8月10日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到桂林处理文革问题。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发来电报,决定派韦国清到桂林全权解决桂林的文革问题。8月18日,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到广西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代表区党委宣布:撤销黄云的市委书记职务,撤销徐为楷的市委副书记和市文革小组长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市委副书记。听到宣布后,师生们高兴极了,顿时欢呼声和口号声响成一片。当乔晓光宣布结束后,一些学生马上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押上汔车开到市区内游行。大批学生跟着汔车上街,沿途高呼“打倒徐为楷”,“坚决拥护区党委的正确决定”,“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等口号,一时间,整个山城轰动了。这是桂林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重大事件。 对于广西师院学生们的造反举动,那时桂林市的许多人是无法理解的,对文革运动也尚不理解,因而反工作队、打倒徐为楷、炮轰桂林市委、炮轰区党委、戴高帽游街等等举动,都是无法理解和容忍的。人们在疑虙,这不是和1957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样了吗?因而多数人对此是怀疑的,反对的。也有一些好心的人在为学生们的所作所为担心受怕;然而,那时也不乏有少数人是支持学生们的。 在文革的初期,桂林市各大中学校都是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各学校间互不来往。现在师院的学生们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对桂林各学校和广大市民影响极大,此时人们涌向街头,涌向师院内去看大字报,把整个桂林闹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们争相看大字报,特别是中央领导入关于文革运动的讲话,一些人并在认真的作记录。 师院的学生则三三两两的在校园内和大街上发表演讲,阐明他们关于文革的各种问题和自己的观点,号召人们起来反对那些阻碍文革运动的领导干部,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对于学生们的这些举动,遭到了许多人的围攻,他们指责学生们的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右派翻天”,与学生们展开激烈的辩论。更有桂林市委和区党委指令驻桂林的部队出动宣传车与同学们相对抗,组织干部和工人围攻学生。八月份正是桂林的盛夏时节,天气炎热,但人们的政治热情比这天气更热。往往几名师院的学生被数十人以至数百人围在中间。名曰辩论,实则是在围攻,不准学生离开,学生们长时间连水都没有喝的,这就是最初状态的群众斗群众,完全是市委和区党委一手组织策划的。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数日,把个原来平静的山城桂林轰动起来了。市民们在一起,即使是一家人在一起,谈论的话题都是师院学生上街游行、大字报和徐为楷戴高帽游街之事。在这些议论中,同情的、支持学生的有之,但是更多的则是不理解或者是反对的。不论是哪一种意见,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热情似乎是调动起来了。 学生们从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了解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保护少数,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了中央的这些指示,一些头脑敏感的人,特别是一些像杨先生一类的青年知识份子开始思考桂林以至广西的问题了,觉得学生们的作法是对的。有这种认识的人慢慢的多起来了。 面对桂林出现的问题,桂林市委及广西区党委的领导们,感到桂林的问题是严重的,他们显然不愿看到广西师院学生们的这种行动继续发展下去,更不要波及到广西其它的地方。为了控制这种局面,区党委一方面决定撤销文革工作队,一方面又留下观察员监视学校的动态。八月下旬的一天,桂林市委在中心体育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区党委撤销文革工作队的决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会议的最后是请韦国清讲话。韦国清是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员,这样级别的高官在桂林亮相,可见当时区党委对桂林问题的重视和忧虑。韦国清本来到桂林多天了,住在104部队,派部队宣传车上街和组织群众对师院学生的围攻本来就是他指使的,他对桂林的情况十分了解。然而,当着数万名与会群众,他竟敢当面说谎。什么他“昨天刚从北京到桂林”,对桂林的情况还不了解;“要求同学们要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开展文化大革命,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运动,提高警惕,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和利用。”韦国清的撒谎很快被人揭穿,他的讲话也遭到学生们有力的抨击。 自八月下旬以来,外地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大学生不断来到桂林进行串联,他们带来了北京的许多资讯,并把北京的一些作法带到了桂林,这对桂林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他们与师院的学生们的结合,增强了桂林学生们的力量和信心。此时的大字报更多了,不但贴满了校园,大街上主要街道都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大字报的内容也逐步升级,从打倒徐为楷到打倒黄云,从打倒伍晋南到炮轰韦国清,斗争的矛头向上,且愈来愈激烈。一些善良的人们看了大字报直摇头,不知学生们要搞到什么地方为止;但也有不少人看后觉得十分过瘾,认为学生们有胆量,有水准。 北京学生的到来,他们手臂上都戴了红卫兵的袖套,身穿黄军装,手拿红宝书,肩背小垮包,显示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朝气与青春的活力。这些都成了桂林学生们的楷模。很快师院的学生们依照北京红卫兵的样子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久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集中火力,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桂林市委,指向了广西区党委。 直到此时,桂林市委和区党委仍然认为师院学生们的行动定是受到坏人指使的,其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与之坚决斗争,揭露操纵他们的幕后指挥者的阴谋。为此,市委在学校中组织另外的学生成立“红旗红卫兵”组织,在机关职工和工厂中成立“工人赤卫队”,与师院学生和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相对抗,从而再次挑起了不同观点两派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桂林市委和区党委的授意和支持下,红旗红卫兵和工人赤子队在街头上贴出了不少反对师院“老多”的大字报,诬称师院“老多”是“右派闹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大字报则指名道姓说某人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子”在搞阶级报复,某人又是什么“野心家”、“投机分子”等等。有些敢于公开表态支持师院学生的干部、职工则遭到指责和围攻,少数人则被本单位领导打成“反革命”而遭到迫害。文革初期的“枪打出头鸟”,在桂林是较为普遍的。桂林附近的一些县城,当地领导更有组织群众大会来声讨师院“老多”的。桂林的事态发展就显得愈来愈严重了。 围攻和声讨,都是在桂林市委和区党委的指挥下进行的,目的是制造白色恐怖给学生们施压。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吓倒学生,相反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对立情绪。为了抗争,学生们不但写出了更多的大字报,并且于九月七日到桂林市委大院内开展绝食静坐斗争,要求市委承认和检讨认错,不许围攻学生,此举使桂林及广西的领导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连续三天的绝食静坐,把个桂林市闹得满城风雨,市委的领导们则更是躲避不敢出面。但一些学校和单位声援学生们绝食静坐斗争的大字报和游行队伍不断增多。面对此种局面,市委领导则是躲在后面,组织红旗红卫兵与工人赤卫队与之对抗。市委组织人数更多的队伍,出动多辆宣传车,不分白天与黑夜地在街上乱跑乱叫,高音喇叭声不绝入耳,……但最终市委迫于形势的压力,答应与学生们对话,静坐绝食终于取得了胜利。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毛泽东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次接见百万学生和红卫兵,其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又连续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支持学生们四处串联,到处造反,把整个中国都搞乱了。特别是《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三、十四、十五期,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终资产阶级反动路垮台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造反派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出现了所谓的“一月革命”进行夺权斗争,自此造反派似乎取得了胜利。此举影响到了全国,各地都相继出现了夺权斗争。此时的广西文革运动也跟着出现了新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桂林,此时的保守派彻底垮台,造反派是翻身了,成了主宰桂林形势主力军,杨福廷、周兆祥……等一批造反派的组织领导者则成了时代的风云人物,受到了桂林人民的广泛称赞、热议与关注。
二、1967年广西两派的斗争再起
1967年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后,毛泽东支持“告反派”夺权,号召各地建立“三结合”的新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此举影响到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进行了夺权斗争,使文化革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桂林,“老多”派胜利了,成了主导桂林形势的主力军,受到市民的广泛称赞。特别是驻桂林的6955部队奉命介入文革运动支左,全力支持“老多”,使“老多”成了一支响当当的造反派队伍。从1967年的3月起,6955部队派出官兵到各学校开展军训,使桂林出现了一个平静、安宁的大好形势。此时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的记者到桂林采访,报纸上第一次出现了赞杨桂林“老多”的文字。 文革运动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此时在广西首府南宁出现了新的情况,区党委和政府一批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谢王冈——等人站出来亮相,相继犮表了“2‧19”和“4‧19”声明,表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检讨错误,支援造反派;但此举不但并未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相反在广州军区的主导下,他们却公开做“让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此时韦国清并未检查自己的错误,也未取得群众的谅解,遭到了南宁造反派的反对,认为这是“把韦国清抬出来”,继续压制造反派,因而极力抵制。此时军区则大力扶持原来已经垮台了的保守派,要他们支持韦国清,这就激怒了造反派,他们组织人马到广西日报静坐,并于1967年4月22日成立“422火线指挥部”(这就是此后“422”名称的由来),反对军区的错误作法。此时已经垮台的保守派则重新集结起来,成立“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联指”名称的由来),公开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此举影响到了广西各地,各军分区和县武装部也效法组织成立“联指”派,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由此,在全广西范围内,“联指”派“支韦打伍”,“422”派“支伍打韦”,两派自此出现了新的斗争。 随着两派斗争的发展,6月13日首先在南宁出现了武斗,并影响到了全广西,许多地方都相继出现了武斗,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并影响到了铁路交通中断。为了增强力量在武斗中取胜,7月13日南宁的“联指”派组织数百人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驻桂6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六0炮一门,弹药一批,这是广西首次出现的抢枪事件。8月4日,“联指”派又调动上万武装人员围攻广西日报、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派的据点,此后又围攻工人医院和民族电影院“422”派据点,使“422”派处于受压制和打击的处境。南宁的武斗影响到了全广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两派武斗的紧张形势,并影响到铁路交通一度中断。 面对此种情况,杨福廷等“老多”派领导人决定派出人员奔赴南宁,支持“422”派,并组织大批人员在6955部队支持下到铁路沿线护路,维护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此举受到了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各级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广泛称赞。 然而此时的桂林,“老多”派虽占绝对优势,但受南宁的影响,原来已垮台的保守派极少数人也重新集结成立桂林的“联指”派,在桂林市区内他们无法立足,就跑到’”联指”派力量强大的阳朔、荔甫、永福、鹿寨等县去活动,不时窜到桂林附近抢劫、打人,并杀害“老多”派一名公车司机,激起了桂林广大市民的愤恨。为了武装自卫,“老多”派也于8月10日到桂林军分区抢夺武噐,此举被称之为“810”行动。其后不久,驻桂林的6955部队的军人全付武装在市区游行,全力支持“老多”派,大长了桂林“老多”的志气,受到了桂林百姓们的欢迎。 介于当时广西两派斗争动乱不堪的形势,中央为了稳定广西的形势,促进两派的大联合,就组织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到北京学习、谈判。从6月至11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曾八次接见两派代表。在接见中周总理曾说“422”派确实激进,确实敢于造反,特别是称赞了桂林“老多”派;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派则有所批玶。那时杨福廷先生作为桂林“老多”派代表团负责人,也被代表们推选为“广西422代表团”负责人,亲自参加了周总理的8次接见,深感当时周总理和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使他十分髙兴,深受鼓舞,感到自己责任之重大。 经过两派代表在北京的学习和谈判,在中央主持下,两派达成了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同时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都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把广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此基础上,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欧治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55军军长)、焦红光(空七军军长)、郝忠云(6955部队副师长)、王斌(104部队长)、伍晋南(区党委文教书记)、安平生(区党委副书记)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和生产,把广西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 杨先生说,两派实现大联合,“区革筹”的成立,这是一件大好事,从此广西的形势会变好,各地“422”派受压的处境将会改变,他和许多人一样内心里是很高兴的。从北京回到桂林后,他当即召开“老多”派各级负责人会议,传达上级的指示及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分析广西当前的形势,研究讨论下一步文革的工作,虽然在桂林“老多”派占绝对优势,但我们要高姿态,平等的对待“联指”派,真诚地与对方实现两派的大联合,建立桂林市的“革委会”。
三、1968年的大武斗及遍布全广西的凶杀惨案
广西两派实现了大联合,“区革筹”的成立,“422”派的人们以为形势从此会变好,他们的内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但事物的发展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越来越糟,使人大为失望。就在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决定”下达和“区革筹”成立的同时,广西的一些地方就多次出现“联指”派进攻“422”派的事件,并出现乱杀人的惨案。到了1968年的春季,这种事件不但没有被制止,反倒有扩大的趋势。如广西的全州、荔莆、宜山、玉林、陆川、梧州、钦州、灵山、上思、甯明、罗城、巴马……等等许多县、市,都出现过多起这样的事件。那时执掌广西大权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他们在口头上也喊两句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杀人”的空话,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来制止,对杀人凶手更没有进行任何处理,一些当权者甚至对这些事件暗中支持、甚或是公开支持,终使广西的形势发展愈日恶化。 在南宁、柳州这两座“422”派力量强大的城市,“联指”派也多次挑起事端,企图消灭“422”派,逼迫”422”派不得已要起来自卫,使,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老多”派占绝对优势的桂林,“联指”派也敢于屡屡挑起事端,寻衅闹事。虽然在1968年4月中旬桂林市革委会和桂林地区革委会先后成立了,并且两派均有对等的代表成了革委会的委员,杨福廷先生还是桂林市革委会的常委,但桂林的形势在“联指”派的挑动下也愈益紧张。1968年5月4日,“联指”派首先在市区内抢占据点,并从5月10日起先后15次到104部队、301部队、警备司令部、军分区、6955部队、空军机场、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抢夺枪支弹药。与此同时桂林地区“联指”也先后9次抢夺武器,使桂林的武斗形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联指”派的此种非法之举,地、市革委会却置之不理,任其事态的发展。此时“老多”派被迫无奈也作出相应的反应,从5月23日起也在市区占据点,到6955部队和军分区抢夺武器,用于武装自卫。在两派武斗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地、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却搬迁到“联指”派控制的南站地区,表明他们是公开的站在“联指”派一边,支持“联指”准备围歼桂林“老多”派,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们的用心所在。 原来广西“联指”派的头目、幕后指挥者及韦国清这个广西的土皇帝,他们早已定下了“消灭‘422’,建立革委会”的方针,他们在各地围歼“422”派,杀人放火,逼迫各地“422”派人员为了逃命而上山下乡躲藏,有的则逃到“422”派力量强大的南宁、柳州和桂林这三座城市求生。此时“联指’派则大肆制造舆论,宣称什么”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是‘伍修集团’的最后堡垒”,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集中地,为此他们就调动农民进城围攻这三座城市,并派部队全力进行围歼。恰在此时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于6月17日发布破获“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习称“6‧17公告),并造谣说“有的‘422’派头目就是反共救国团的成员”,“反共救国团就在‘422’派据点内”;为此他们在全广西各地到处围歼“422”派,杀人放火,却反诬说什么是“‘422’派搞反革命爆乱,杀人放火”,以此向中央谎报军情,当年的《广西日报》也极力配合,大造舆论,介绍各地围歼、杀人的经验。所有这些,终于骗取中央下达“7‧3布告”,使他们获得了尚方宝剑,由此一场歼灭“422”派、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终于在广西全面展开,最终使”422”派和桂林”老多”派被歼灭,十多万生灵惨遭杀害,是广西有史以来罕见的大灾难。 杨先生说,4月中旬桂林市革委会成立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那时两派表面上是和平相处的。但5月4日“联指”派突然在市区抢占据点,接着又抢夺部队的武器,使形势急转直下,武斗一触即发。此时我们得到情报,桂林地区12个县的“联指”派在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指挥下,正在组织一万多人的队伍准备围攻桂林,使“老多”派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此种情况下,桂林市革委会主任王斌(104部队负责人,“区革筹”领导成员之一)曾叫我搬到南站“联指”派控制区,为我提供住房,他的汔车随便我用。之前他也曾几次请我吃饭,我与他的个人关系还是好的。但此时全广西的“422”派都处在受围攻的处境,桂林“老多”也处在危难之时,我怎能背叛“老多”离开自己的岗位呢? 在12县“联指”派武装围攻桂林之前,经“老多”派负责人会议决定,派我上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以求得说明,5月下旬的一天我即乘火车离开桂林前往北京。到京后即与桂林电话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我走后两天火车即中断了,12县的“联指”武装一万多人已经对桂林形成了包围圈,“老多”的武装正在准备反击,以粉碎“联指”派的围攻。 在北京时杨先生曾到中央文革上访,反映桂林遭受围攻的情况,但并未得到任何答复。期间杨先生曾返回到长沙,想找6955部队的领导求得帮助。因为此时6955部队的郝忠云副师长及在他们学校参加过军训的张团长和孙政委正在长沙参加广州军区举办的学习班,杨先生与他们相熟,想从他们那里了解有关情况,求他们给予说明。在长沙杨先生见到了郝、张、孙这三位部队领导人,郝副师长明确对杨先生表明,说上面有指示,不准再过问桂林文革之事,也不准再接见任何一派的人员。介于此种情况,杨先生明白了其意,这是上级的决定,只好无奈地离开他们。但第二天晚上孙政委亲自到杨先生所住的旅馆来找他面谈,告诉他桂林的事上面不给他们管了,说是围歼广西“422”是定了的,至于桂林,只要“老多”保持不动,不主动反击,最后的结局不会像“422”派一样,希望杨先生能返回桂林做工作,以挽救危局。 孙政委是好心,说的也是实情,但此时到广西的火车不通,他不可能回去,当时孙政委曾叫他化装成军人回桂林,但也不可能通过全州“联指”派的检查站,是回不了桂林的。权衡再三,他只有再返回北京继续上访。 不久中央派飞机把南宁、柳州“422”派主要负责人和桂林“老多”派负责人接到北京,办“学习班”,实际上是对“422”和“老多”的严厉批评。杨先生与他们见面后,住到了一起参加学习班的活动。7月3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7月25日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都是一味指责“422”和“老多”派的,并不准我们讲话申辩,与1967年的八次接见完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使杨先生一班人心里很难过。 7月25日接见后,南宁、柳州的“422”头目在北京即被抓捕,桂林“老多”的刘振林、刘天偿也被抓捕。8月24日杨先生与广西两派代表回到南宁,26日在南宁参加了广西区革委会成立大会,8月30日晩回到桂林,第二天即被禁止外出而失去自由,9月3日被五花大绑在桂林游斗,游斗中险些被打死。此后多次被批斗,被管制监督劳动近八年,失去自由,是人生最痛苦的八年。
四、对广西“文革”运动几个问题的认识思考 桂林“老多”是一支优秀的”造反派”队伍
杨先生说,文革前他对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是有诸多不满的,但他相信党和 毛主席,认为这些问题是地方干部胡乱作为造成的,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对此他感到无可奈何,平时只好默不作声,埋头于学习和工作。文革中是毛主席的讲话和支持鼓舞了他,与他具有的人权、自由、民主的思想形成了某种巧合,才使他成为了激进的造反者. 他是怀着一颗为社会的进步与公平、正义,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有自由民 主的权利而投身于“文革”运动的,从来不想到什么个人的目的。他带领桂林”老多”这支“造反派”队伍,平心而论可称得上是一支优秀的“造反派”队伍。在整个“文革”运动过程中,纵观这支队伍的种种表现,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支队伍都有它的特殊之处,可以说是一支守纪律的文明之师,深得百姓们的称赞。因为这支队伍有别于外省许多地方的“造反派”,特别是像上海、北京这些地方的“造反派”,他们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乃至毛泽东的支持下,破“四旧”、抄家、抓人、打人、-甚至把人打死……等等,干了不少错事、坏事,是不为人称道的;而桂林“老多”不论是在“文革”初期处于受压制、打击的处境,还是在夺权翻身后的日子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发生。当然,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他们也会出现过一些错误,如喊过一些过激的口号,给徐为楷、黄云、韦国清……等等领导干部戴高帽游街等过激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但这是那个时代、是毛泽东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这群天真的青年人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
意想不到的迫害与屠杀
1968年的广西大武斗、以及伴随而来的大屠杀惨案的发生,是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杨福廷先生说,他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回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投身于“文革”运动之中,带领师生们起来革命、造反,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劳碌奔波,没有怨言。但想不到广西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大武斗及大屠杀惨案,全广西的“造反派”队伍被歼灭,十多万的生灵被残杀;就自己个人来说,1968年8月25日与广西两派赴京代表一起从北京回到南宁,26日参加了广西区革委会的成立大会,29日从南宁回到桂林,30日被非法抓捕关押,9月3日遭到非法的游斗,在游斗中险些丧命。其后失去自由,遭受监管劳动八年,这些至今仍然叫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广西会出现如此悲惨的局面呢? 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联指”派的坏头头、幕后指挥者、及广西的当权者韦国清们造成的,他们是历史的罪人,理应受到历史的惩罚与清算,但至今为止,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处遗”中惩办了极少数凶手以外,以韦国清为首的一批人,他们的种种罪孽至今仍未得到彻底的清算,是令人愤恨与不解的。 回顾“文革”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中央文革的领导者们在1966、1967年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何以到了1968年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置“造反派”于死地呢?就全国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探讨。从广西来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悲惨的局面,毛、周及中央文革那些当权者当然是有责任的,是和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邪说是分不开的,但直接的罪责则是韦国清一手制造的,韦国清是广西文革的千古罪人,是人们必须清醒认识的。 广西大屠杀确是太悲惨了,十多万生灵死于非命,那些许许多多的杀人惨况用语言是难于表达的。当年的凶手们随意抓人、打人、杀人是极为普遍的,杀人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残忍无比,人世间罕见。有用木棍打死,石头砸死,用刀捅死,五花大绑丢下河溺死,生埋活人,生割活人,挖心肝、吃人肉,五马分尸,有对妇女先强奸后杀死,有全家被杀绝、家产被抢光的……等等,历代以来的酷刑几乎都用上了,是至今为止仍然叫人无法相信,无法理解的,但却是血淋淋的真实存在。
广西的“文革处遗”及其给世人留下的思考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然而在广西,这个传统是被彻底地破坏了。十多万的生灵惨遭屠杀,在“文革”结束后,因为韦国清及他的势力仍在广西当政,大屠杀本来就是他们制造的,要他们自已来处自己是绝不可能的。嗣后韦国清调到广州、北京升迁了,他的继承者们当政,也同样不可能处理。只是到了“文革”结束多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各方的强烈要求下,特别是受难者家属及子女的频频上访申诉,在中央的干预下,才被迫作了“文革处遗”工作,给无辜惨死者平反招雪,恢复名誉;对杀人凶手的处理,全广西只有十名凶手被惩办判死刑,十四名凶手被判死缓,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只有1841人,对绝大多数凶手和责任人则不追究刑事责任,只作党纪、政纪的处分的有47,671人。这虽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世人仍是不满意的,尤其是受难者家属及子女更为不满,又显得无可奈何。 另外,一些幕后指挥者或者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一些人,他们不但根本就未受到任何处分,反倒被升官了,如像韦国清、岑国荣,王建勋、李嵋山、颜景堂、曹铁军、陈秉德、廖炜雄、段振邦……等等一大批人,这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其实大屠杀本身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当时的革委会、武装部、军分区乃至区革筹、广西军区,都是各级执掌大权的领导机关,他们不强力的制止武斗和乱杀人,相反却发出针对“422”派及桂林“老多”派的《通告》和《公告》之类的政府公文,并通过媒体鼓吹杀人理论,调动农民进城,调动部队、甚至带队围剿屠杀“造反派”,这不是政府行为又是什么?个别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面对种种围剿、屠杀,他们看到了,听到了,却不出面制止,都是罪责难逃的。 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这个政府又有何用呢?许多事情就是政府出面做的,政府和它的领导者公然站到了杀人凶手一边。直到“文革处遗”的时候,也未见哪一级政府和哪一位领导人站出来向受难者家属和受迫害的人说一句道歉的话,他们的人性和人道到哪里去了!? 特别是在那个疯狂与荒唐的年代里,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群众之手”杀人,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的邪说杀人,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存在,未得到彻底的批判。一些人当年虽未参予打人、杀人,但他们在傍边围观,有的还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内心有愧和自责,对“文革”的种种罪孽毫无认识和反省,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 4、值得反思的民族 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人类社会早就步入文明时代了,怎么在1968年的广西还会出现“返古’现象,回到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呢?这令人会想到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的“劣根性”问题。诚然我们这个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勤劳、朴实、勇敢的民族,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和科学技木,为世界人类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有许多优秀分子是功载史册,受到了世人的称赞。然而我们这个民族(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是存在丑陋、愚昧和凶残之一面的,即所谓的“劣根性”问题。古代和中世纪之事我们姑且不论的话,就以近代和现代的一些事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表现是十分典型的。 就以二十世纪开始之事来说吧,1900年的拳匪暴乱,那些愚昧无知、生性残忍的暴民,他们视现代文明为“妖孽”,为此他们倒电线杆、撬铁轨、毁教堂、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不论男女老少都杀无赦,真乃无法无天,毁灭文明。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国家的耻辱。 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在一些搞共产爆力革命的地区,如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安徽、陕西等省的一些地方,出现抢夺地主财产,分地主的田地,甚至杀地主;等到地主们组织还乡团随国民党军打回来时,地主还乡团也大肆报复屠杀抢夺他们财产的农民。这种农民和地主间的互相残杀,使这些地方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这是谁之罪呢? 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时,斗地主,分他们的田地和财产,把地主扫地出门,甚至杀地主,一些人表现的是那么残忍和没有人性,这是为什么呢? 至于文革中的乱打人、乱杀人,更是与时俱进;尤其在广西,杀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是历史罕见的,一些人是那么地愚昧和凶残,这个民族中的一些人怎么了,这个民族不值得反思么? 所有这些,反映出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问题,这在一些人的身上是确实存在的。一些人的愚昧无知,盲从,自私,鲁莽,简单粗暴,凶恶残忍,一旦接受了某种邪魔思想的宣传鼓动,他们就会产生无比的狂热而干出种种伤天害理的蠢事来,这是为无数的事实所证实了的事。如义和团的胡作非为,一些斗地主、杀地主的疯狂之徒,“文革”的杀人狂徒,这些都是我们民族中“劣根性”的典型表现。 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已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为了钱,一些人什么坏事、丑事都可以干得出来,诸如偷盗、抢劫、投毒、杀人、放火、制假贩假、走私、贩毒、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等等,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么? 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大问题。所有的人都应该关爱生命,珍惜生活,切不可做伤天害理之事。任何时候都不要盲从、紧跟,不要自私、凶恶、残忍,而应该多动脑筋想问题,从人类共有的人权、民主、自甴的普世价值入首来思考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以和平、理性、博爱、不害人……等等这些原则来思考和行事。只有如此,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
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度绝不会发生“文革”之类的灾难
人们知道,当今的世界有共和国、王国、公国、大公国、联邦、合众国、酋长国、教皇国等诸多不同的国家,但就其社会制度来说,却只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究竟谁优谁劣,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的实践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答案: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是宪政民主的政体,所以它是当今世畀上最好的社会制度。尽管它们有不足之处待改正,但仍不惜为当今人类较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则是无疑的。 人们记得,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共产宣传甚嚣尘上,直逼广大劳苦大众辘辘的饥肠,以苏俄为首的共产集团大搞共产暴力革命,声称要健立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先后在苏俄、东欧各国、亚洲和中美洲的一些国家都建立了共产政权,在实践社会主义,有的声称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又大喊大叫什么“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已是日落西山,气息淹淹,走到了腐朽没落的末路”。 社会实践的结果完全与他们宣称的相反,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气息淹淹,腐朽没落,反倒是蒸蒸日上,成了当今世界人类的共同追求。而号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却是一个个相继垮台,都走上了(或正在走)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既使有少数仍在宣称自己是什么“社会主义”,也已是名存实亡,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 所有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的,所实行的都是宪政民主的政体,多党竞争执政,三权分立,由公民用选票来决定国家各级机构领导者的人选,公民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绝不会有强制拆迁、强征土地的事件发生,更不会有随意抓人、打人、乱杀无辜的惨案发生。这都是那些号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独裁专制国家所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正是由于在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下,才不断地发生著各种各样的惨剧。在广西,再加上韦国清这个土皇帝的专横拔扈,才导致了大武斗和伴随期间大屠杀惨案的发生。这是植得永远牢记和总结的历史教训,值得世人深入认识和反思的大问题。 假如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像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之类的惨剧还会发生么?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国家,才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大灾难发生,这是必然的。 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宪政民主的政体,这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更是中国人的共同追求。那些高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声称“六不搞”的人们,应该猛醒吧!要知道这一套骗人的说教和作法害苦了中国人,是注定走不通的死路。 —— 以上是我与杨先生几次接触交谈后集成的文字,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相同的。杨先生的人生经历是令人同情和称赞的,“文革”中他为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战,其后惨遭迫害多年。七十年代末恢复自由后,他热心于教学和古典文学的编著,成了颇有成就的一名教授。而今退休了,过着平淡的老年生活,仍然关心“文革”史的研究,关心国家大事,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感谢杨先生的热情款待,感谢他为我提供的许多“文革”宝贵史料。 作于2018年7月初至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