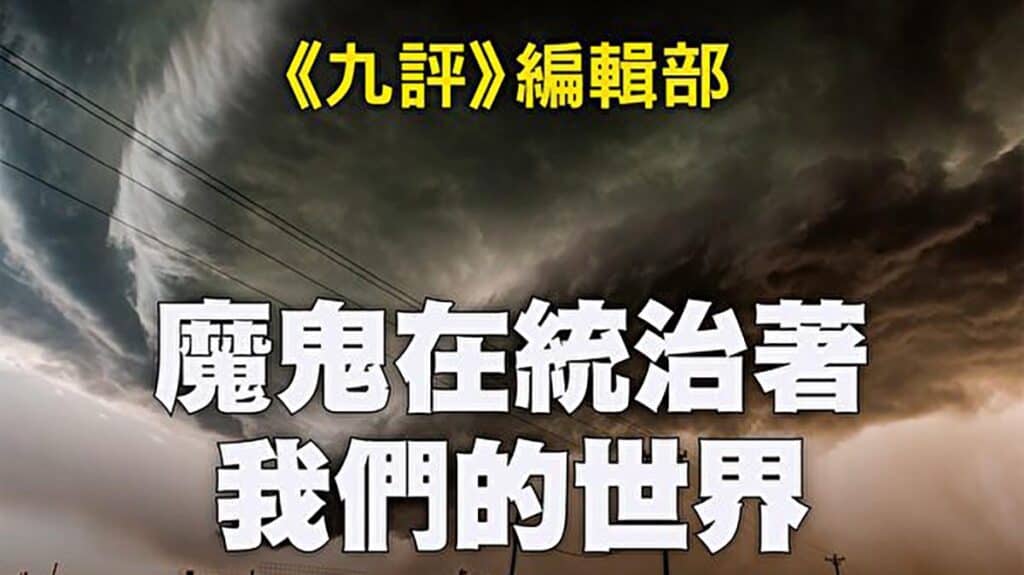陈懋蘅老人说,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她问起过土改,她也从来没有向人说起过土改。“造孽呀,造孽呀——”,她反复地说着这句话,眼中噙满了泪水。
我是“春华秋实”的人,在老家忠县,只要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春华秋实”的。“春华秋实”是我家大门上石刻的四个大字,是我们陈家大院的别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从各地寄来的信件,不需要写街道门牌,只要写上“忠县春华秋实”六个字,邮递员就能准确投递到我家。
父母做主,很早就将我许配给了天堑乡著名绅士陶华轩的儿子陶奎。陶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陶华轩有三个弟弟,叫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
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当时陶奎刚从朝阳大学毕业,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我在重庆读书的懋新弟弟多次写信说,与一个地主家的婚约应该作废,但是我父亲是饱读诗书之人,坚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可失信于人,坚决要履行婚约。
新婚之初,我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要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两亲家都很高兴。
但是,当年冬天土改开始了,这种日子也就很快过去了。
我公公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有100石租的田产,分给三个儿,陶奎名下有30多石,当然就都是地主了。
按照当时的政策,应该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成份,我是解放后才结婚的人,本来无论如何都不该划为地主的。但是由于我丈夫是地主,他身体不好,每月一次的训话会,我就代他去参加,结果我就成了地主。他不到四十就因为饿饭得肿病死了,我就只有把地主当老了。我也申诉过好多次,说我不是地主,但是哪个听你的,我只有怨自己命苦。
当时的政策是减租退押,分地主的财产。民兵们涌到我们家来,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了,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当果实了。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也是果实。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斗争会斗争地主。他们把我公公吊起来打。你知道怎么吊吗?你想都想不出来。他们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你想,那是好痛!
寒冬腊月,民兵们把我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我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造孽呀!我们全部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
我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我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你说怎么受得了。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造孽呀……
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他和天堑乡的乡长很熟,就给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陶奎就这样被撤了校长职务,开除回家。
积极分子们硬要陶奎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积极分子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他和我偷偷地相对痛哭。
那时天天都在开斗争大会吊打人,而且只要吊打人,就要把大人娃儿都喊去看,越是打得凶就越是要大家都去看,说是发动群众。吓死人啊!
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争,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去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积极分子还发明了一种叫“舞转转”的刑罚,就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把朱耀庭老婆的手抓住一只,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就是那种只有三寸长的尖尖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她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不会就此放过她,过了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民兵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唉,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
我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我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天天吊打。快要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
到了腊月三十,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回来。——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事前并没有告知他们,只是叫他们背着铺盖卷沿河边走。临近神溪口时,远远的看见河滩上搭起了公审台,几个人才明白。我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我们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过年了,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我家陶奎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而且是很顾面子的人,过年过节的时候去走村要饭,是多么难受的事!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就死去了。
1961年,陶奎饿死。留下我和几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根据陈仁德(陈懋衡是陈仁德的六姑妈)的记述,爷爷1962年7月死于饥饿。因为自己坚持履行婚约,致使女儿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爷爷在遗嘱中写道:“今已无可奈何!惟有死后坐十八层地狱以抵罪耳。”临终前,他坚持着翻开已经写好的遗嘱,用颤抖的手,艰难的握住笔,在后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补抄》:“衡女身体不强,无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饥寒之险,在所难逃。我死之后,希望嫂嫂和内侄们大力照顾,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年5月1 日写。”